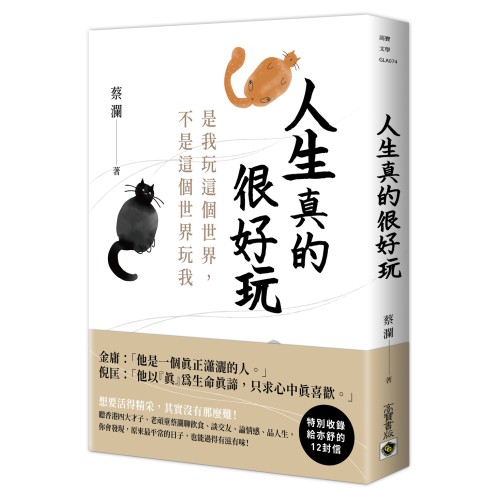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得主 蛇從革 最新力作
★《長安十二時辰》作者、文字鬼才 馬伯庸
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得主 董潤年
中國明星作家榜榜首、編劇、演員 李誕
──一致推薦
★開創東方克蘇魯小說,魔幻寫實風格,挑戰想像極限
「這本書並不只是沉甸甸的現實,也不僅僅是輕飄飄的幻想,它把現實和幻想結合得非常完整。」――馬伯庸
那些在長江逝去的人,
一直生活在跟我們一樣的城市裡,
只是並非同一個世界。
「我喜歡看著水面,總覺得水面之下是另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是我從來不知道的宇宙。這是我的祕密。」
傳說有兩個世界沿著長江江水比鄰而居,一個在江面上,一個在江面下。這兩個世界在水運重鎮宜昌交會,每到夏日汛期,江面下的居民就會浮出水面,以朦朧細雨為掩護,穿梭於往來人群之間,尋找著足以填飽轆轆飢腸的靈魂。
葉江死了,一如十二歲那年夏天,我的好友嚴茂淹死在長江裡,或許,我們從來不曾真正逃脫那年夏日的夢魘。嚴茂的死,改變了我們五個孩子的人生,我們失去了幾乎可以失去的一切,包括性命。然而,對其他同伴而言,這不過是悲慘世界的縮影,但對我來說卻絕非這麼單純,因為我親眼看見,嚴茂以另一種姿態,從長江水面下回來了……
【甫出版即攻占各大書籍榜單】
★豆瓣高分榜TOP 3
★當當懸疑小說飆升榜TOP 1
★當當懸疑小說新書榜日榜TOP 1
★閱文探照燈書評人獎11月類型小說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11月好書
★騰訊華文好書12月書目
★微博小說閱讀榜週榜TOP 3
★「志怪mook」2021年第8期志怪書單
★中文科幻數據庫、科幻百科、《星雲科幻評論》2021年度科幻圖書TOP 20
【媒體書評一致盛讚】
「(《長江之神:化生》)所呈現的畫面,能夠將寫實和超現實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在之前中國是沒有過的,非常值得看!」——秦昊
「在克蘇魯(Cthulhu)的東方化這一點上,我認為《長江之神:化生》是一個現階段的範本。我希望借助《長江之神》,發現、總結乃至構想一套『東方克蘇魯』的創作方法論,為這場颶風的登陸和深入掃清障礙。」——文學評論家賈想
「真實世界同所謂的『幽冥世界』之間,出現了奇特的『對位+錯位』關係……也正是在這種交疊、錯位之中,《長江之神》完成了其克蘇魯風格的本土化過程。」——文學評論家李壯
【讀者好評】
⚫ 老蛇的文字總是有那種魅力,那種通過描寫,讓你在現實中找到原形的魅力。
⚫ 因為太過真實,所以很難分清現實與魔幻的界限。我連續三個夜裡讀完,拿起來就放不下。關了燈,閉上眼,總覺得天花板上和床邊有水怪在緩緩爬行。
⚫ 看上去講的是鬼怪故事,實際上寫的是人心。故事線飽滿豐富,可讀性一流。
⚫ 不得不說看到中間部分時,確實有種後背發毛的閱讀感受。
⚫ 神祕的氣息和快節奏的故事情節讓人欲罷不能。
序章
我的好朋友嚴茂,在二〇〇一年一個週六下午,淹死在長江。
那一天是農曆七月十四,鬼節。
他在長江邊失蹤的那個晚上,夏月的奶奶又一次鄭重告誡我們長江裡有恐怖的水怪。
長江裡有水怪,這是我們當地小孩都知道的恐怖禁忌:雨後深夜,若見到穿著蓑衣、彎腰駝背的人站立在街角,不要靠近,更不要搭訕。
水怪悄無聲息地從長江爬上岸,在雨水中伸展著佝僂的身體,收起背鰭,舒展關節,化為人形,在岸邊找到漁民的蓑衣,披在身上,戴上斗笠,潛入黑暗中的城市街道。
雨夜中,水怪與人無異,只有久經歷練的老人能分辨出來。水怪有雙詭異的大腳,長著彎曲猙獰的趾甲。腳趾粗長,連著腳蹼,黑夜也無法掩飾。
水怪平常很少上岸,只有在水裡找不到食物,餓極了,他們才會扮作人,躲在城市的街道上尋找體弱力微的兒童和女人。
農曆七月,長江裡的水怪會全部爬到岸上,在城市裡到處穿行,尋找從閻王爺生死簿上看來的人名,叫喊這些名字。一旦被叫的人回應了水怪,水怪就會勾住受害者的靈魂,將其帶回長江。這是水怪們每年一度的歡快節日,就像――夏月奶奶神神祕祕地跟我們說――就像我們過春節一樣……
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嚴茂的人。那天十分燥熱,空氣中彌漫著悶熱的霧靄,從長江一直籠罩到整個港務局家屬區。那個中午,我和他,以及另一個夥伴于力舟,在六碼頭附近的江邊釣魚。
江水突然湧動起來,我的眼睛因為正午的陽光從江面上反射過來,而感覺一陣刺痛。一片白灼耀眼之後,我看到在我釣竿盡頭的水面下,一個長著長長綠毛的手臂緩慢地朝我揮動著。
我害怕了,堅持要離開。于力舟立即贊同,他早早就找了一個紙盒頂在頭頂,一個小時之前就想離開了。不過嚴茂一動不動地看著他的釣竿,用行動拒絕了我的建議。
我和于力舟離開江邊。等走出一大段路之後,我再回頭看向嚴茂,似乎看到他穿著蓑衣,頭戴斗笠,如同國畫裡的釣魚老翁。我當時以為自己眼花,燥熱也讓我失去好奇心,就和于力舟離開了。
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回去察看究竟,而是認為自己的眼睛有問題,看走了眼。往後我仔細回想,嚴茂可能在我回頭之前這短短的幾分鐘裡,就已經被水怪拉下長江成了替死鬼。我之所以這麼想,或許是因為這樣能讓我稍微不那麼內疚。二〇〇一年,我還只是個十二歲的孩子,十二歲是一個會為自己的過失找藉口的年齡。其實現在看來,這也是成年人的本能。
六個小時後,在港務局家屬區,家家戶戶都在平房或筒子樓的公共廚房做飯,嚴茂的母親這才發現自己的兒子還沒有回家。嚴茂的母親一開始並不著急,她做好了飯菜,等待兒子回來吃飯。她看了一會兒電視,眼角餘光瞥見嚴茂回到家,坐在客廳的飯桌旁狼吞虎嚥。嚴茂的母親平時不會因為看電視而耽誤吃飯,可是一天卻鬼迷心竅地專注看新聞。她後來回憶,當時她看到嚴茂身上溼漉漉的,以此來佐證自己真的看到兒子回到家中。
然而這卻讓她錯失了跟兒子見最後一面的機會。
等《新聞聯播》結束後,嚴茂的母親發現飯桌上的飯菜沒有動過的痕跡,嚴茂已經消失不見,或者根本就沒有出現過,而桌子和地上積滿了渾濁的水漬。
這很反常,嚴茂是一個很乖的孩子,吃完晚飯後一定會在家裡寫暑假作業。嚴茂的母親開始對自己的所見產生懷疑。她詢問鄰居葉大俊的妻子,葉妻靠在門口,神情恍惚地告訴嚴茂的母親,她剛才似乎看見一個穿戴斗笠和蓑衣的人,站在平房門前……葉妻用她已經混沌的腦袋思考一會兒,又說,不,那個人穿著冬天的校服,站了一陣子後才離開。
嚴茂的母親從他們家――港務新村第六排平房的左手邊第四個堂口――穿過長長的巷道,走到我們的港務局子弟學校操場。學校在港務局住宅區的中心地帶,無論是不是假期,學生和街頭的小混混都會在學校操場上廝混。
操場上沒有嚴茂,只有一群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在打籃球。嚴茂的母親看到了葉江和葉寧兩兄妹。天色漸漸昏暗,葉江坐在草地上,就著球場的燈光複習功課,葉寧則在操場上盪秋千。
葉江告訴嚴茂的母親,他一整天都沒有看到嚴茂,不過可以到海員俱樂部去找一找。海員俱樂部是港務局的工人文化中心,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叫海員俱樂部,而不是水手俱樂部。港務局的男性職工幾乎都是水手,但是他們只能在內河(也就是長江)的船上工作,從來沒有去過大海。海員俱樂部有康樂棋、撞球桌、舞廳,甚至有電影院,大廳裡還有空調。
嚴茂的母親走下住宅區的一條坡道,過了大馬路,經過游泳池、燈光球場和職工醫院之後,到達海員俱樂部。在俱樂部裡,嚴茂的母親看到了我和于力舟。我和于力舟兩人正在打電動。我記得是「街霸」,不然就是「雷電」,俱樂部裡只有這兩臺遊戲機,港務局大部分職工的男孩都會在這裡度過炎熱的暑假。
嚴茂的母親穿過圍觀的小孩子們,問我和于力舟有沒有看見嚴茂。我和于力舟正全神貫注地打電動,于力舟頭也不回地告訴嚴茂的母親,中午我們和嚴茂去江邊釣魚,釣了沒多久,大概十二點半,我們兩人受不了烈日的照射,放棄釣魚,轉而回來打電動。
嚴茂的母親沉默了一會兒,又問我們他在哪裡釣魚。
我說應該在七碼頭和六碼頭之間那一帶吧,嚴茂說那裡比較好釣。
氣氛突然變得凝重,我和于力舟回頭看向嚴茂的母親,她的身體顫抖著。她拉住于力舟的手臂說:「能不能告訴你爸爸,讓他帶人去河邊找嚴茂。」
一旁的電玩遊戲室老闆老張說:「我打電話給于所長,你趕緊去江邊。」
嚴茂的母親隨後去了江邊。過了十分鐘,我和于力舟意識到問題嚴重,放棄遊戲通關的機會,趕往六碼頭江邊。我們到達的時候,一群人正浩浩蕩蕩地從江邊走向公路。其中一個男人背著已經暈厥的嚴茂的母親。我們走近江邊,在刺眼的緊急照明燈下,看到了嚴茂遺落在江邊石頭上的釣竿。
接著于力舟的父親于所長來了,帶著手底下七八個員警。人群紛紛讓開,于所長盯著釣竿和衣服看了很久,對手下說:「通知打撈隊吧,孩子已經沒了。」
晚上九點,我和于力舟,還有趕來的葉江和葉寧,站在黑夜的江邊。在巨大的探照燈照射下,江灘上無數的蚊蠅昆蟲在光線中飛舞。我們看著打撈隊員套上笨重的潛水用具,走入江水之中,去摸索嚴茂的屍體。江水淹沒了打撈隊員的身體,我握緊了拳頭,內心緊張,我的夥伴們也跟我一樣。
嚴茂是我們的朋友,可是他死了。我們對死亡一無所知,只有一片漆黑的無力感。
副所長老秦看到我和于力舟以及葉江兄妹站在江邊,便對于所長低聲說了幾句話。于所長走到我們面前,喝斥了于力舟兩句,接著派一個員警開車,把我們送回港務局家屬住宅區。
我們的家都在這個占地廣大的港務局住宅區裡,住宅區坐落在方圓幾公里的一片小山地帶,其中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平房建築和兩三層高的筒子樓,唯一的高樓是我們學校旁的爛尾樓,在整個住宅區中央顯得鶴立雞群。
嚴茂意外死亡讓我們幾個小孩的心情都難以平復,我們不曾如此近距離地面對死亡,所以都不願意回家。暑假期間,父母親管得比較沒那麼嚴,會讓孩子晚上在住宅區遊蕩。
葉江和葉寧的父親葉大俊正在和妻子打架。葉江的母親吸毒,下午她又拿了家裡的錢購買白粉,注射在手臂靜脈裡。而那筆錢,是葉大俊剛剛拿到的工資。
葉江兄妹決定到我家來睡一晚,避免父母拿他們兩人當出氣筒。
于力舟的父親老于所長忙著打撈嚴茂的屍體,他的母親是個溫和的女人,看到于力舟已經回到筒子樓樓下,也就不再追問于力舟什麼時候回家,只是叮囑我們注意安全;而我父母則是去武漢研習,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陷入驚慌的我們去了夏月家。夏月的家也是平房,在嚴茂家後面兩排。
我們走到夏月家的窗口前,敲了一下窗戶。夏月把窗戶打開,于力舟輕聲地說:「嚴茂淹死了。」夏月的臉色頓時在燈光下變得煞白,喃喃地說了句:這怎麼可能。
天空突然劈下一道閃電,整個港務局家屬住宅區瞬間閃過一片極亮的白光,白光穿透了所有的建築和人,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彼此肉身裡的骨骸。緊接著,幾乎貼著我們的頭皮,響起了一聲劈天裂地的巨響。
我們全都嚇壞了,摀著耳朵蹲在地上。隨即傾盆暴雨擊打在玻璃上,瞬間把我們從頭到腳淋溼。
炸雷之後,隆隆的雷聲持續了一會兒,彷彿空中有個可怕的妖魔,發出低沉的吼聲。雷聲停歇,夏月立即打開大門,讓我們進入堂口。這是一個平房的公用客廳,四家共用,堆放著雜物。夏月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色T恤,胸口有一個卡通圖案,剛發育的胸部在T恤下顯露,我能清楚看見兩點凸起,頓時心慌意亂。
我走神的片刻,夏月已經咬著嘴脣,身體發抖,焦急地問我們:「是真的嗎?」
于力舟點點頭。
夏月忍不住抽泣起來,我和于力舟突然意識到我們再也見不到嚴茂了,但是我竟然不敢哭出聲來,因為恐懼遠遠超過了悲傷。
我們幾乎從生下來就認識,現在其中一個夥伴死去,讓我們不知所措。
我和嚴茂、于力舟同一年出生在港務局的職工醫院,兩歲就進入子弟幼稚園就讀,又在子弟學校的小學上到初中。
我們住在同一個區域,一起上學,一起長大。一個幾乎每天都在你生命中出現的人死了,這個意外超出我對生活的認知。
我們幾個人站在堂口,屋外大雨瓢潑,雷聲隱隱約約從遠方傳來,讓我們更加恐懼。
堂口的角落裡發出一聲遲緩的呻吟,我和于力舟嚇得跳了起來。
「是奶奶。」夏月立即安撫我們。
我和于力舟這才看到,在昏暗的燈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裡,夏月的奶奶正躺在涼椅上,她又呻吟了一聲。夏月回到屋裡,拿了兩袋頭疼粉交給奶奶。奶奶撕開頭疼粉倒進嘴裡,呻吟聲慢慢停止。
夏月的奶奶有頭痛的毛病,從我們有記憶起,她就不停在吃這種醫務室開的藥物。我對頭疼粉並不陌生,知道那其實就是嗎啡類的藥物。整個港務新村裡魚龍混雜,很多吸毒的外地人在毒癮發作的時候,都會用這個藥物替代。葉江的父親很會做菜,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在燉湯裡加入放幾包頭疼粉。
夏月的奶奶盯著我們幾個小孩看了很久。她已經很老了,臉上的皺紋把五官都掩蓋在褶皺之中。我們一直很害怕夏月的奶奶,因為她每次看著我們的目光都充滿寒意,而且她身上有一股難以言說的泥土腐爛味,長大後我才知道,那就是死亡的氣味。
要不是我們都喜歡夏月,是斷然不會到夏家這個堂口來的。
夏月的奶奶開口說話了:「小茂被長江裡的水怪拉下去了?」
這句話讓我們毛骨悚然。
長江裡的水怪,是的,長江裡有水怪,夏月的奶奶已經告訴我們很多次了。
奶奶看著我們說:「今天是七月十四,長江裡的水怪和鬼都會爬到岸上,你們不要亂跑,他們會把你們都拉下去的,就跟小茂一樣。」
我們都被夏月的奶奶嚇到了,夏月的奶奶繼續說:「嚴茂這個孩子,印堂本來有顆福痣,可惜眼睛下面、鼻梁四白穴上又長了一顆淚痣,福氣都沒了,命是肯定不長的。」
七月十四是鬼節,我立即意識到于力舟的父親于所長為什麼要把我們送回家。我下意識地看了看屋外,大雨中的巷子盡頭,一個模糊的人影撐著雨傘,站在雨中一動不動。我的眼睛又開始不受控制,變得極度敏銳,穿過雨簾,在黑夜就著路燈看見那個人影穿著一件校服,我忍不住輕呼一聲:「嚴茂……」
那人轉身,面朝向我,我看見那張沒有鼻梁的慘白臉孔,印堂和眼睛下的黑痣清晰可見。
水怪!
我尖叫起來。
夏月的奶奶嗤嗤地發出笑聲。
于力舟和葉江也跟我一樣朝屋外看去,穿著校服的人影已經消失在大雨之中。
雨停之後,于力舟的母親找到夏月家,把于力舟領了回去。我和葉江、葉寧回到我住的筒子樓。葉江很喜歡我家,因為客廳的書架上擺滿了書籍。葉江每次來,都會抱著書安靜地閱讀。他家裡沒有書,他的父親葉大俊不喜歡書,也不喜歡葉江看書。
我點上蚊香,跟以往一樣,我和葉江睡在客廳,葉寧睡在涼臺。我家只有一個臥室,而我父母臥室的門永遠緊閉。
即便是嚴茂死去的變故,也不能阻擋葉江看書的興致。這讓我覺得葉江是不是太過冷漠了,或者這是葉江下意識逃避壓力的行為,我無端地揣測著。
葉寧的肚子發出一陣奇怪的聲響,我意識到他們兄妹應該還沒有吃飯。
我在廚房裡煮了一鍋麵條,三個人拌著醬油吃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葉寧一個人在涼臺上害怕,要求跟我和葉江交換,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覺,於是我和葉江只能一起擠在涼臺那張折疊床上。
雨又下了起來,黑暗中,葉江說:「嚴茂是死了,還是被水怪抓到長江裡去了?」
我突然全身寒毛直豎:「外面似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葉江用手摀住我的嘴:「夏月的奶奶說過,晚上有人叫你,千萬不要回應,特別是今天晚上。」
我躺下,風雨中似乎仍然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我坐起身,隔著涼臺玻璃看向外面。
「我什麼都看不見。」葉江結結巴巴,「但是我聽得到。你不要看……」
然而我的目光已經被樓下的人吸引,那個撐著傘、穿著校服的人抱著大槐樹的中段,身體距離地面兩三公尺。他抬著頭,撐著傘看向我。目光與我對上後,他扔掉雨傘,一邊呼喚我,一邊四肢交替,順著樹幹向上爬。
葉江摀住耳朵,而我則把自己的嘴巴摀住。
穿著校服的人是嚴茂嗎?現在他已經爬到樹枝上了,他轉過頭對著我們咧嘴笑了一下,隨後一陣風刮來,他如同水霧一般消失在大雨之中。
我們身後突然響起葉寧的聲音:「哥哥,你在叫我嗎?」
葉江大叫一聲,飛奔到客廳,葉寧的聲音從葉江的指縫間傳來:「我在這裡,是媽媽嗎?」
葉江狠狠地把葉寧的嘴巴摀住,但是一切都太遲了。屋內外又是一片閃亮,隨即陷入黑暗。一陣轟隆的雷聲過後,屋內最微弱的檯燈突然熄滅,整個港務局住宅區全部停電,只有路口高處的變壓器在雨水中閃爍著妖冶的藍色電光和火焰。
我們三個小孩子抱在一起,在黑暗裡瑟瑟發抖,祈禱黑夜趕快過去。
尺寸(公分)21*14.8*1.92cm
開本 25
頁數 384
序章
一
二
三
四









印簽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卷四)_立體書-500x500.jpg)
千門之聖+書腰-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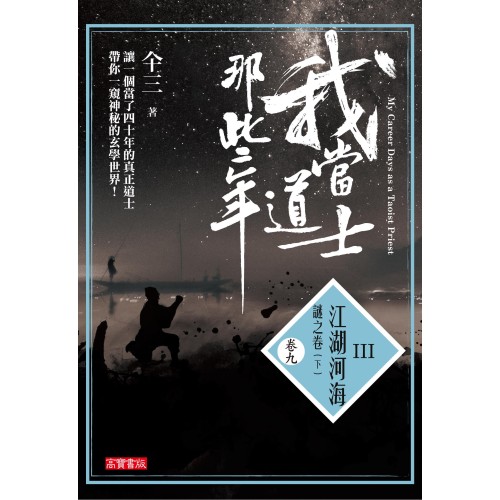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