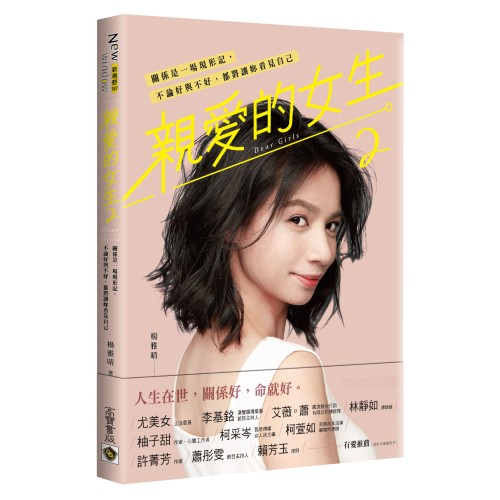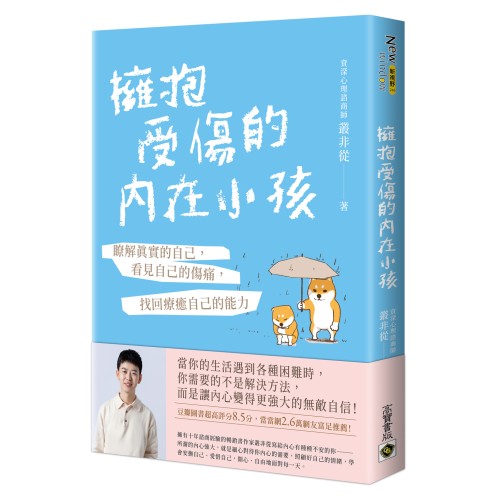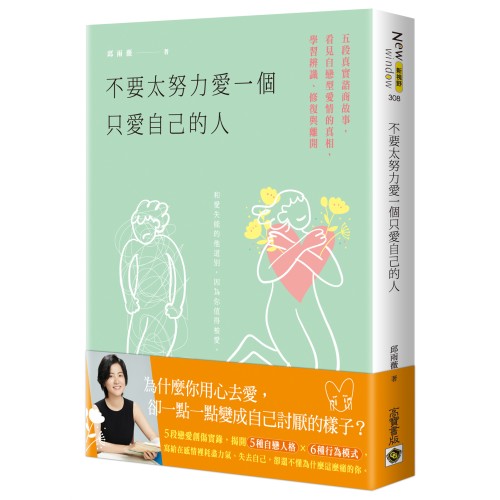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那天,砍傷他的那一刀,讓他從此與手術臺無緣……
在不平與埋怨面前,他選擇將光明捧在手中,帶著善良與堅毅,向光而行。
豆瓣圖書8.8分,當當網100%好評,63,000人熱淚盈眶推薦,
一本感動千萬讀者,最具生命力量的細膩之作!
附繁體中文版獨家印刷簽名名句典藏扉頁!
▍當當2020年文學暢銷排名No.1
▍中國亞馬遜2020年新書榜No.1
▍豆瓣2020年年度高分圖書8.8分
▍榮獲新京報2020年職業寫作之書、南方都市報年度十大好書、中國出版商務週報2020最具話題度十大圖書、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20年度影響力圖書、微信讀書2020年度好書,各大讀書平臺強力推薦!
2020年春節前夕,一場飛來橫禍,讓陶勇醫師成了新聞人物。
陶醫師坐診期間,突然遭積怨已久的病人行凶砍傷,此事引起醫界嘩然,也成為各大媒體與民眾的關注焦點。
如此受人景仰、給予希望與新生的醫師,從此再也無法上手術臺救治病人……行凶者砍傷的不只是醫師能進行精密手術的雙手,也傷害了一個個需要治療的病人、無數個懷抱希望的家庭。
當眾人的目光放在醫患關係緊張、暴力衝突應該受到制裁的同時,在加護病房靜養的陶醫師則將此事視為一段獨特的經歷、一場在生死邊界的考驗,這也讓他對自己從醫的使命更加堅定。
他用乾淨細膩的筆觸寫出醫生與病人之間相互成就的感動故事,不只表達了對醫學的熱愛,也寫下了面對挫折與打擊的時候,道出關於醫患關係、生死善惡、哲學探索、充實自我、追求幸福等人生的思考與感悟。
回顧從醫二十年的經歷,他說:「從醫是一場修行,這條路艱辛又漫長。因為上天給了我一次重生的機會,我想用我的餘生去創造更多價值,去幫助更多的人。」
在這本書中,你會看到人性的善良,也能體會生命的意義。
陶醫師想治好每個人的病,也想醫好每個人的心。
他相信希望與愛可以治癒世間一切的苦難,相信每一雙眼睛的背後,都是光明。
【陶勇心懷至善的從醫信念】
面對仇恨與「惡」,我選擇用真誠的初心與「善」來面對。
現實或許不像我們想像中理想,但也不至於走到最低劣的結局。
世界如此美好,值得我走這一遭,
我不是神,但在未來的道路上,願意繼續發出我的微光。
【真誠推薦】
酷勒客-clerk的路障生活/不點醫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藥劑科主任/李銘嘉
臨床心理師/劉仲彬
張德芬空間創辦人、作家/張德芬
演員/孫儷
作家/周國平
作家/賈平凹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倪萍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
一個有真信仰、真愛、真事業的人,是世間任何力量都打不敗的。
──作家、《只眷戀這人間煙火》作者 周國平
這本書講述的其實不僅僅是陶勇醫生的職業故事,正如一個瞳孔裡可以看到一片宇宙一樣,這本書裡也有一個宇宙。關於生死、善惡、堅守、初心,甚至孤獨、幸福……從生死場走過的陶勇醫生會又一次刷新你對他的認知!
──演員 孫儷
人性複雜,善惡總在一念之間,陶勇所呈現出的通達與大智慧,絢爛奪目。他的眼裡有光,是因為他眼中有最初的善良和正直,照亮那些有信仰的人。我永遠為這樣的人熱淚盈眶。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倪萍
陶勇醫生的故事,不該是一個人的戰鬥,我們該用抗疫的態度來面對暴力傷醫。
──中央電視臺《新聞1+1》主持人 白岩松
《目光》一書,實為一名眼科醫生對人心、對世界的觀察與所悟。拳拳之心;切切之情,讓人動容。思維之廣,遠見之深,讓人驚嘆。
──作家 賈平凹
【當當網讀者含淚推薦】
這本書是陶勇醫生的個人文學隨筆,是一個醫生的沉思錄和成長感悟。如果說醫學研究是關於身體和疾病的思考,《目光》就是陶勇醫生關於人生和內心的洞察。特殊的事件將陶勇醫生以獨特的方式帶到大眾眼前,這本書將帶給讀者心靈的歸途和內心的力量。──小雨讀文學
陶醫生在經歷砍傷事件後,有時間靜下心來寫這些隨筆,大都是自己與患者的經歷,對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悟,文筆細膩流暢,堅毅與柔情共存,這是智慧,這是菩提。──沉默焰火
這本書的出版,伴隨著一個醫生的「死裡逃生」以及從醫多年的寶貴心得。這本書不僅是文學領域的重要作品,更是醫學領域的重要呼籲。陶勇想讓我們看見的是暴力傷醫事件之後,作為醫生與病患兩種角色對醫療體制的反思以及醫患矛盾的反思。──喵發財咪
讀完陶醫生《目光》這本書,思緒萬千。無妄之災帶給他的似乎是更堅定的信念,對他人的友善、對病患的關愛、對自己的反省、對科研的熱愛、對哲學的思索,是這本書的主題。沒有刻意放大那場襲擊帶來的悲慘,沒有刻意渲染心中的不解和憤怒,沒有刻意引導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就連康復中的痛苦也只是一筆帶過,我卻為此數次落淚,為陶醫生遭遇的不公,為小岳岳不放棄生的希望,為天賜和天賜爸爸的不屈,為老奶奶終於找到回家的路……太多太多的悲憤不知從何而來。──upazdtjdrfk
【陶勇醫生的行醫人生守則】
碰傷我的石頭,我沒有必要對它拳打腳踢,而是要搬開它,繼續前行。
用愛的意念去對待他人、對待世界,這種磁場同樣會吸引到愛。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身邊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榜樣,他身上一定有你不具備的優點值得去學習。
善與惡是相對而論的,完全的「善」會把人變得軟弱,完全的「惡」會將人推向地獄,只有將「善」與「惡」的標準與底線確立,才能構成一個和諧的自我。
人生在世,世事無常,誰也無法把握明天,只有懷揣一顆希望的火種才能照亮迷茫。
堅強,不是受過一次打擊後站起來,而是經過無數次打擊後,還能站起來,仍然微笑著告訴生活,放馬過來吧。
不管是哪種孤獨,我認為都是客觀存在的,最主要的是面對孤獨時,如何能看清它的本源,取其長去其短,將孤獨化為一種成就自我的力量。
人生的意義是難以找到精準答案的,既然這個問題是無解的,那不如與自己和解,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大概就是活著的意義。
用有限的生命去面對無限的知識,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不斷地探索和深耕,從而充盈自己的內心,讓自己回顧自己一生時,無愧無悔。
用積極的心態去擁抱不確定性,給自己一個強大的信念,才是通往幸福的必備條件。不把某種目標當作幸福的唯一砝碼,而是用一種正念的心態去面對當下,用樂觀的心態去構建未來,這種人往往無論取得什麼結果,內心都是幸福的。
「過去屬於死神,現在屬於自己」,真正的快樂並不是源於勝利的那一刻,而是源於那個不斷提升和成長的過程。
每個人都是平凡人,只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擁有一份堅定的信念和面對挫折的勇氣,才是真正的平凡英雄。
01緣起:至暗時刻
既然決定活下去了,那就要迎接更激烈、更殘酷的戰鬥,我是有這個準備的。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臨近春節,醫院裡依然人滿為患,儼然沒有任何節日來臨前的氣氛,病痛不會因為任何過節假日而放緩腳步。
早上臨出門時,妻子叮囑我,母親今晚準備了我最愛吃的香菇米線,讓我早點回家;同時,車子的電瓶故障也有一陣子了,需要早點修,以備春節期間使用,我答應了。事實上,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兌現這個承諾。好像家是我唯一可以撒謊的地方,在醫院,我不敢有一絲言語的誤差,因為對每個病人來說,醫生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讓他產生無限猜想。
今天是我出門診的日子,坐到就診臺後,我查了一下今天的門診量,比昨天還多十幾個,護士跑過來和我說,還有幾個病人請求加號看診。我笑了一下,香菇米線看來是吃不成了,能多讓幾個病人踏實地過年也不枉母親的一番苦心。
整個上午看診還算順利,看了有一大半的患者。我心裡不禁有些舒暢,想著也許晚上能趕回去吃飯,所以我中午沒去員工餐廳吃飯,想下午儘量早點開診,就簡單地泡了一包泡麵,吃完後稍微休息了一會兒,大概一點鐘便開診了。
下午的第一位患者,雙眼紅得像兔子眼睛,一問才知道,是因為玩電腦遊戲熬了幾天幾夜沒睡覺,我叮囑他多休息,幫他開了一點消炎藥。有心說,這樣的病完全沒必要大費周章跑到這裡來看,任何一個小門診或者社區醫院都可以診治。但又一想,對於患者來說,他們也無法判定病情嚴重與否,往往會往最壞的方向去想,他們來了也是求個心安。
第二位是老患者了,結核炎引起的眼底損害,八年了,病情一直反反復復。患者老家醫療條件不佳,便在北京的一家海鮮餐廳工作。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廚師,後來才知道是電工,包吃包住,一個月三千元人民幣。我心下感嘆真是不容易啊,便照例把他的掛號費取消了。聊起來才知道,為了多賺一點春節期間的加班費,他今年不準備回家過年了,我於心不忍,便把上午患者送來的一袋小米轉送給他,但願他在北京過的這個年,能順遂溫暖。
第三位是複診患者,她是一位投資人的母親,之前因為眼睛發炎找不出原因,心急如焚;後來視力變得越來越模糊,幾近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輾轉各地找到我這裡。我為她安排了眼內液檢測,今天的結果顯示病毒量明顯升高,證實了我之前的判斷,終於找到病因。
第四位是個年輕的女患者,由她母親陪同,病情比較複雜,雙眼在一週的時間內快速失明,同時伴有頭疼、耳鳴。她們拿著過往厚厚的一疊病歷和報告,我逐一認真翻閱了一會兒,想找出其中的關鍵問題。這時候,我隱約看到有一個人進了診療室,徑直走到我的身後,我也沒多想,這樣的情況在醫院太過常見──雖然有護理師,但有時病人也會趁其不備跑進來插隊問診。
猛然間,我感覺後腦遭到狠狠一記重擊,就像被人用棒球棍用力砸了一下,整個腦袋磕到辦公桌上,頭「嗡」的一下,一種木木的昏眩感襲來。我下意識抬手護住頭,那時我的右手還拿著病人的病歷,所以本能地用左手向後腦去摸。
緊接著又是一擊,力度更勝之前,我聽到旁邊的病人大叫一聲,這才意識到我被襲擊了,便慌忙站起來往外跑。原本我的工作位置是靠近門的,但為了方便查看X光片,我特意把座位調到了離X光片燈箱更近的右側位置,沒想到對逃離造成了阻礙。
我甩開周邊的人和物,衝出來直奔樓梯處,走廊裡瞬間傳來厲聲尖叫,人群四散。我眼睛餘光看到自己的白大褂已是殷紅一片,頭還在嗡嗡作響,眼前金花閃爍,耳內轟鳴,整個人像吃了迷藥一樣暈眩。
我努力控制著自己的身體,拚命奔跑,實則這個過程不過十幾秒鐘。我跑到樓梯口的轉角處發現這是一個死路,剛要轉向,對方已完全近身,電光石火之間,我看到他手裡拿著一個明晃晃的凶器,便本能地抱住頭顱,重擊再次襲來,我整個人被擊倒在地。
我大聲呼救間,看到一個白色身影撲了過來,與那人扭打在一起,我趁機爬起來往手扶梯那跑去,跌跌撞撞跑下樓梯。這時我已經神志不清,迎面看到一位護士,她驚愕地看著我,然後迅速扶起我,連扶帶背地將我拖進一個辦公室,然後將門反鎖。
她又驚又急地對我說:「您受傷了,趕緊躺下!」然後扶我躺在辦公室的看診床上。我整個人在驚嚇之餘還算冷靜,我看到她動作迅速地拿出酒精、紗布、剪刀開始為我消毒包紮,這時我才看到我的雙臂和手已是血肉模糊,左臂和左手上的肉翻捲開來,露出白骨。
事發太過突然,很多細節已記不清楚。事後在恢復的過程中,我才陸續瞭解了整個事情的經過。對方提的是一把大型菜刀,非常沉重鋒利,我在診療室就被砍了兩刀,一刀在我後腦部位,另一刀就是我的左臂小臂處。在我奔逃到樓梯轉角處時,我被砍翻在地,那時我的後脖頸又中一刀,左手可能在下意識擋刀時被橫著劈開,右臂也中了一刀。
而在這短短的幾十秒鐘裡,同在診療室的一位志願者為了喝止行凶者,在我跑出去後,後腦被砍了兩刀;而一位正坐在診療室門口候診的病人家屬的手背,也在為我阻擋行凶者的時候挨了一刀。
那個衝出來與歹徒英勇搏鬥的,是坐在我斜對面診療室的楊碩醫師。當時他聽到走廊上的異常聲響時,第一時間跑了出來,正看到鮮血淋漓奔逃的我。他下意識就追了上去,追到樓梯轉角處看到已經倒地的我正被歹徒揮刀亂砍。用他的話形容,我發出的聲音是他從未聽過的淒厲慘叫聲,他二話不說就撲上去抱住了歹徒,歹徒扭身甩脫,一刀沖他劈下,他頭一躲,刀鋒劈到他的頭部左側,眼鏡碎裂在地上,左耳被劃開一道長長的口子。
正是他的阻擋給了我逃命的時間,歹徒甩脫他後繼續向我奔逃的方向追去。楊碩醫師赤手空拳,便跑去洗手間一把奪下打掃工人手裡的拖把就又追了出去。此時整個七樓已經空空蕩蕩,人群早已奔逃到各處。他看了一下手裡的拖把,根本沒有殺傷力,就扭身進了一間診療室抄起一把椅子。
在我奔逃的過程中,因為失血太多,身體發軟,根本跑不過歹徒。這時又有一個人衝了過來,他姓趙,是一名物流人員。他看到滿身是血的我,下意識地抄起走廊上的看板衝上來與歹徒對峙。
後來我也是透過員警的筆錄才得知了他的存在,他一直與歹徒英勇對抗,還不時地勸歹徒冷靜,直到我跑得沒蹤沒影了,歹徒才坐下來說:「你報警吧。」很快,值班的保全人員聞訊趕來控制住了歹徒,這位趙姓先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沒有他,我也不會死裡逃生。
我被緊急推往了急救室,開始手術,打過麻藥,我就進入了昏迷狀態。
事後我才知道,當時院長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緊急聯繫了相關醫療室的同事,他們或從診療室或從病房趕來為我救治,積水潭醫院的陳主任也接到了我院的求助電話,從積水潭趕過來。
手術持續了約七個小時,在這期間,幾位醫師同院主管商量了手術方案,開始進行各處傷口的縫合與處理。我的左臂與左手受傷最為嚴重,神經、肌腱、血管兩處斷裂,而陳主任正是手部外科的專家,果斷做出了救治方案。
那時我妻子也從新聞上看到了消息,通知了我的父母,兩位老人坐地鐵來到醫院,我可以想像他們的心情是何其恐慌。相關單位的主管也得到消息趕到了醫院,他們安撫了我的父母,讓他們暫時放心。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麻藥的藥效還未散去,整個人暈暈沉沉,不知道身在何方,只覺得腦袋像被套了一個堅硬的鐵殼,勒得頭痛欲裂。
等再次清醒,我才慢慢恢復意識。我躺在ICU裡,頭上纏滿紗布,身體被固定在床上。透過白色紗布的縫隙,我看到我的兩條手臂被套上堅硬的石膏,身體一動也不能動,頭頂上方掛著點滴瓶,藥水不緊不慢地滴落。
這些,是在我之前的二十年中太過熟悉的場景,而今天我才有機會特別認真地觀察──白色的屋頂上有幾個黑色的斑點;明黃的白熾燈照得整個房間通明空曠;點滴管裡的液體先是慢慢凝聚,然後形成一顆結實的水滴,掙脫管口的束縛重重地滴下,悄無聲息地流入我的身體。
我見過無數個躺在ICU的病人,知道他們的痛苦,更懂得他們求生的欲望。然而,當我自己真實地躺在這裡時,才真正刻骨地體會他們的感受。
我為什麼會躺在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的父母、妻兒他們在哪裡……我通通不得而知。
我被劇烈的頭痛折磨著,也無暇思慮更多。這種疼痛不像平時的疼痛有清晰的位置來源,而是一種又漲又暈、彷彿是一團黑雲死沉沉地壓在頭上的感覺。後來聽護士說,那時我的頭腫脹得比平時還要大了一倍。
這種疼痛讓我如在煉獄,這是一種持久的、完全沒有辦法緩解的疼痛,我昏昏沉沉、半睡半醒,其間不時有護士和醫生過來查看以及問詢,我都記不太清楚。我全身心都在與疼痛抗爭著,只覺得時間過得異常緩慢,彷彿是一個人在煉獄中獨自煎熬。
一直到第三天,我的狀況才漸漸好轉,同時也得到了各方的慰問。只是此時我呼吸困難、氣力微弱,也難以表達太多。
楊碩醫師在被搶救後也被安排在了病房,他放心不下我,偷偷跑過來看我。我看到他頭上的紗布,心裡痛楚,想流眼淚,但似乎連流淚的力氣都沒有。我們就像一起經歷了生死的戰友,目光相對,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主治醫師告知我我已脫離生命危險,讓我放心。事實上,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層面,疼痛讓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睡過去。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妻子來了,她沒有我想像的那樣悲傷,就好像我們平時見面一樣。她笑著對我說:「你知道嗎,你都上微博熱搜了。」這個傻姑娘,也真是符合她的性格,大大咧咧、簡單直接。
我苦笑了一下,特別想問她家裡的情況,可是此時我完全沒有力氣開口。她好像知道我要問什麼,柔聲地告訴我,女兒暫時拜託朋友照顧,父母也安頓好了,一切都好,讓我放心。我心酸不已,但也動不了,只能向她眨了眨眼。我能想像家人們經歷了一場多麼大的震盪,妻子紅紅的眼眶出賣了她的樂觀,我知道她一定晝夜未眠、哭了很多次。
ICU不能久留,妻子陪我聊了一小會兒便被請了出去。
我一個人躺在床上,頭痛仍在持續地折磨著我。我終於知道,原來被利器所傷,第一時間的感覺竟然並不疼,而恢復的過程才是疼痛的高峰。頭疼是腦水腫造成的,我整個腦袋像扣了一個完全不透氣的鋼盔,疼痛不已;我知道這個過程誰也幫不了我,只能靠自己一個人扛下去。
值班護士進來幫我換藥,詢問我的感覺,她笑著說:「你啊,在ICU裡是最輕的,別擔心。」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醫生的謊言只有醫生聽得懂。
一直到第五天,我的頭痛終於有所緩解,至少從憋炸的鋼盔中透進了一絲絲空氣,我清晰地感覺到了疼痛的位置。但我的手臂卻開始出現問題,我感覺到噬骨的寒冷從左臂傳來,像是接了一條冰凍的鐵棒。我驚懼我的左臂是不是已經不在了,直到醫師說手術很成功,神經和肌肉全部被砍斷,縫合後還沒有知覺,需要時間去修復,我才稍微放下心來。
有了意識後,我開始有了維持身體機能的生理需求,妻子替我熬的雞湯我也難以下嚥,勉強喝了幾口便再吃不進去。但也許是吃得太少,我一直沒有大便的便意,我知道,這時候我必須多進食一些,才能加快康復速度,於是接下來每頓飯都儘量勉強自己多吃幾口。
第六天,我又渴望、又害怕的便意來了,我託護士幫我找了一位男看護攙扶我走進洗手間。那是我受傷後第一次下床,身體好像不是自己的,我完全控制不了。看護用了好大的力氣才勉強扶我邁出一小步,病床距洗手間大概也只有三十公尺的距離,但它好像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段路程。
勉強排了一次大便,我心中有些愉悅,終於可以看到一點點曙光──身體戰勝了病痛,它會越來越好。
妻子又來看我,她說現在我上了新聞,很多熱心的人都非常關心我,我的同學、朋友們打爆了她的電話,紛紛錄製祝福影片給我,還有一些人想來看我,但因為新冠疫情沒辦法進入醫院,他們送來的鮮花擺滿了一整條走廊。
她又說:「你知道嗎,柯比墜機去世了,還有他喜歡的女兒也在飛機上,一併走了。真是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誰也不知道。」作為半個球迷的我,心裡無限感傷,不免又對自己感到慶幸,至少我活下來了。妻子問我要不要對網友們說點什麼,因為我微博上的留言都有上萬則了。
疼痛的折磨下,加上聽到疫情和柯比的消息,我心情無比複雜。
從醫生瞬間變為患者,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那些眼病患者是怎樣過來的。眼前出現最多的是那些視障兒童的影子,他們家境並不富裕,甚至可以說一貧如洗,但是也一直堅持,從未放棄過。
此刻,我突然覺得也只有這首詩能代表我的心情:
心中的夢
我,
來自安徽,七歲那年,
一場高燒,讓我再不能看見;
我,
來自河北,從小患有惡性腫瘤,
摘除雙眼;
我,
來自山東,
生下來那裡就是空的,
老人想要把我掐死,
是媽媽緊緊抱住,
給我活下的希望。
陽光和陰影,
我無法區分;
愛情和甜蜜,
我不能擁有。
別人只是偶爾焦慮,
而我們卻一直煩惱,
因為大家口中的美麗,
我們永遠無法知曉。
我很怕,
拿起筷子吃飯的時候,
夾不起菜,
會被譏笑;
我很怕,
走路時不小心碰到旁人,
會被責罵;
當我們用盲杖不停敲打地面,
聒噪的聲音讓別人躲避不及;
當我們打開收音機,
無論怎樣調低電臺的聲音,
在別人的耳朵裡,
總是嫌大。
但是,我心中,
還有一線希望。
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拿著打工賺來的收入,
替父母買一件新衣,
添一雙新襪。
我也希望,
有一天,
膝下也有兒女,
在耳邊,
和我說說悄悄話。
夜深人靜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想家,
掛掉父母的電話,
我能想像,
他們兩鬢的白髮,
還有心中割捨不斷的牽掛。
我會努力,
讓父母不因我是盲人而終生活在陰霾之下,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
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
14.8*21*1.656cm
25 開
推薦序 苦難是美德的機會
推薦序 謝謝你,讓我看到生活中的光
推薦序 陶勇醫生的故事,不該是一個人的戰鬥
第一章 緣起:至暗時刻
第二章 善惡的相對論
第三章 一個醫生的生死觀
第四章 熱愛,自有萬鈞之力
第五章 所謂少年氣
第六章 蒼生大醫
第七章 1%的世界有多大
第八章 暗黑王國的小小人
第九章 那些不為人知的力量
第十章 上善若水
第十一章 世界是怎麼來的
第十二章 認知與接納
第十三章 沉默如雷
第十四章 月亮與貝殼
第十五章 北京,北京
第十六章 四十不惑
第十七章 從春遊到溺水
第十八章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第十九章 未來可期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