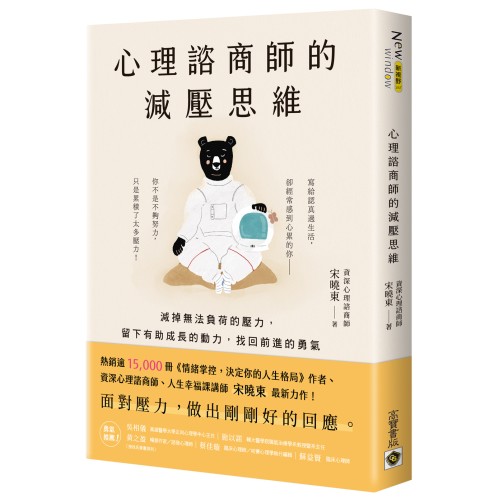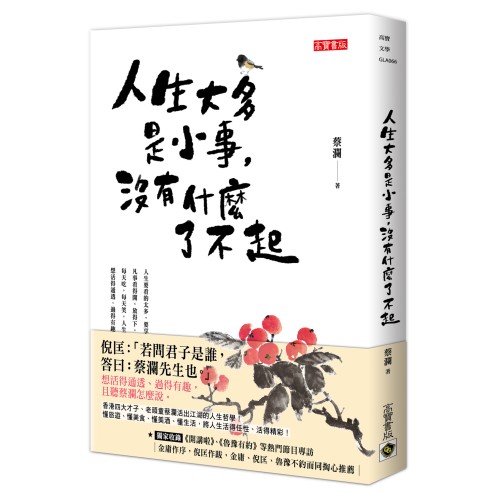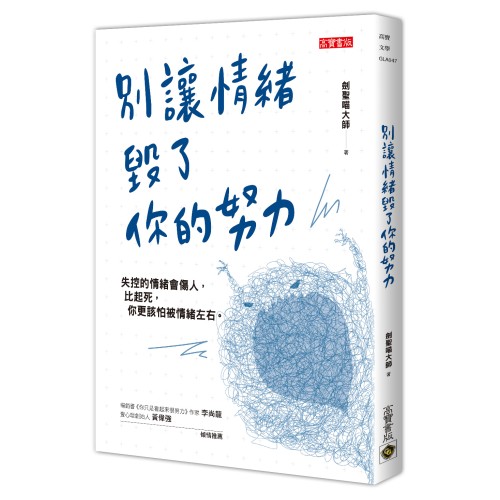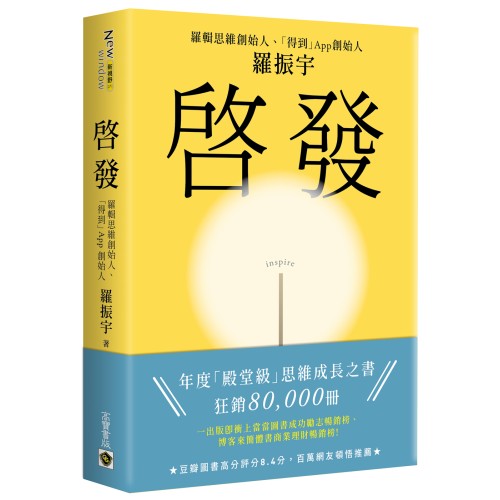會員限定
動物教我成為更好的人:不管有幾隻腳,都要在人生道路上勇敢的前進
NT$253
NT$320
-
作者莎伊・蒙哥馬利 (Sy Montgomery)
-
譯者郭庭瑄
-
繪者蕾貝卡・格林(Rebecca Green)
-
ISBN9789863616993
-
上市時間2019-07-10
-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紐約時報暢銷書
★入圍國家圖書獎作者
╲╲這些動物教會了我一件關於人生的事──那就是「如何做個好人」。╱╱
【國際媒體一致推崇】
「詩人與科學家。」──《紐約時報》
「印地安瓊斯與艾蜜莉狄更生的綜合體。」──《波士頓環球報》
「作者說故事的方式總是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動物如何用溫柔的方式增強我們的人性,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文學回憶錄。」 ──《出版商周刊》
與動物的相遇,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牠們的愛超越所有,帶領我們走過最純真的感動。
還記得養的第一隻狗嗎?
陪伴你成長的貓咪?
動物園看到的各種生物是如何打開我們的眼界呢?
這是一本關於生命,家庭,如何失去和真愛的美麗、療癒的書本。
作者身為大自然冒險者,為了研究書籍,電影和文章,被扎伊爾的一隻憤怒的銀背大猩猩追趕;被哥斯達黎
加的吸血蝙蝠咬傷;在馬尼托巴的一條坑裡看著一萬八千條蛇,並在法屬圭亞那處理了一隻野生狼蛛……
她從豬身上學會了玩耍、邊境牧羊犬教她恩典、野生白鼬讓她學會寬恕,當她人生陷入低潮甚至想自殺時,是樹袋鼠讓她瞭解了真愛。
正因為我們是人類,和「動物」是不同的物種,當我們了解、關懷其他物種時,同時也拓展了我們的道德世界,並且學會擁抱他者。
本書包含作者人生中遇到最特別、美麗、稀有的動物,10則故事帶領我們進入不同的人生課題,最終生命因動物們而變得更美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類。
【感動好評】
「生命的愛與美好,都濃縮在這一篇篇的章節裡。」------ 畫家/黃海蒂
「放下生而為人的身段,謙卑地與大自然對話。渺小如我,而萬物皆師。」----國語日報、泛科學專欄作家/曾文宣
「工作日誌 daily-logbook」粉絲頁作者
「阿鏘的動物日常」粉專版主
圖文作家/蠢羊與奇怪生物
---推薦(按筆畫排列)
探索世界的動機 莫莉
讀小學的時候,除了上課的時間外,我和莫莉總是膩在一起。莫莉是我們家養的蘇格蘭㹴犬,我們倆會在紐約布魯克林漢彌爾頓堡二二五號區的將軍官邸「執勤」,到平坦又寬敞的草坪上站崗,更確切地說是莫莉在看守環境,而我在看顧牠。
不幸的是,對被培育用來獵捕狐狸和獾的蘇格蘭㹴犬來說,秩序井然又講求效率的軍事基地裡根本沒什麼獵物可以抓。基地中每一寸土地都經過嚴謹的整理,完全不容許野生動物的存在;但也有例外,因為我們住的房子是美國陸軍的財產,不是自己的,不能擅自蓋籬笆或圍欄,每當偶爾出現松鼠時,莫莉總會衝出去追牠,我們只好在草地上深深插進一根堅固的螺旋樁,再用狗鍊把莫莉拴在上面。看著牠用濕濕的黑鼻子和高高豎起、不停轉動的尖耳朵仔細觀察環境,我心裡湧起一股非常、非常強烈的渴望(其實我每天都有這種渴望),希望自己能跟牠一樣有嗅聞、傾聽遠方動物來來去去的能力。就在這個時候,莫莉突然暴衝,看起來就像毛茸茸的小砲彈。剎那間,那根四十五公分長的螺旋樁就咻地飛出草地;莫莉一邊齜牙咧嘴,發出又喜又怒的吼叫聲,一邊拖著狗鍊和螺旋樁狂奔,穿過單層磚房前的紫杉樹叢。我馬上就瞥見牠在追什麼了───是兔子!
我立刻跳了起來。我以前從來沒看過野兔,從來沒有人聽說過漢彌爾頓堡有野兔! 我想靠近一點看,可是莫莉已經追兔子追到磚房前面了,我那兩隻瘦弱又被困在瑪莉珍皮鞋裡的小學二年級生的腳,根本沒辦法跑得跟牠那四條有爪且發育成熟的腿一樣快。
蘇格蘭㹴犬的叫聲既兇猛又低沉,而且威嚴十足,想不注意都難。很快地,我母親和一位負責維持將軍官邸整潔的士兵從我們住的那一區跑了出來,我身邊頓時冒出好幾雙大人的腿,大家都緊追著那隻瘋狂猛衝的㹴犬跑來跑去(當然啦,他們完全追不上牠)。這時莫莉早就掙脫狗鍊,把螺旋樁遠遠拋在身後了。牠拚命往前跑,擋也擋不住,任何人事物都無法阻止牠。不管有沒有抓到兔子,牠都會在外面晃上好幾個小時,或許天黑後才會回家也說不定。等牠玩夠了、準備好了,牠就會出現在家門口簡單地叫一聲,要我們讓牠進去。
我好希望自己能跑去追牠。我不是想讓牠停下來,而是想跟牠一起跑。我想再看看那隻兔子;我想知道夜晚的軍事要塞是什麼味道;我想遇見其他狗狗,和牠們追逐打鬧;我想把鼻子探進洞穴聞聞看是誰住在那裡,也想發掘深埋在泥土裡的寶藏。
很多小女孩都很崇拜自己的姊姊,我也不例外,只不過我姊姊是隻蘇格蘭㹴犬,而我,穿著媽媽幫我換的蕾絲襪子和荷葉邊洋裝無助地站在那裡的我,只想變得跟牠一樣:強悍,充滿野性,而且勢不可擋。
根據我母親的說法,我一直都不是什麼「正常」的孩子。關於這點,她舉了一個例子佐證。她和我父親第一次帶我去動物園的時候,才剛學會走路的我就掙脫他們的手,搖搖晃晃地走向自己選的目的地───猛獸區的圍欄裡,裡面關著園區中體型最大、最危險的動物。我猜那些河馬當時一定是用和善的眼神望著我,不想把我踩扁或咬成兩半(重達一千三百六十多公斤的河馬很有可能會這麼做),因為不知怎的,我爸媽最後成功把我從圍欄裡救出來,而且毫髮無傷,但我母親卻一直沒有從這場意外中復原,真正放下這件事。
我一直都很愛動物,對我來說,動物的吸引力遠勝過其他小孩、大人或洋娃娃,我比較喜歡看我養的兩隻金魚「小金」和「小黑」,或是跟我心愛卻命運多舛的烏龜「黃眼女士」一起玩(我母親來自南方,早在女性主義崛起前,我就從她那裡學到這個語言習慣,用「女士」來尊稱所有女性和雌性動物)。黃眼女士就跟一九五○年代大多數的寵物龜一樣飽受飲食失衡所苦,導致龜殼軟化而死亡。母親送了一個洋娃娃想安慰我,但我完全不理,也不想跟它玩;我父親從美國南部回來時帶了一隻凱門鱷(鱷魚的一種)造型的填充玩偶給我,我立刻替玩偶換上洋娃娃的衣服,然後用娃娃車推著玩偶到處跑。
身為獨生女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或渴望有弟弟和妹妹。我不需要其他小孩的陪伴。大多數的小孩都很吵又很好動,完全坐不住,只會跑來跑去,把那些在人行道上昂首闊步的鴿子嚇得到處亂飛,要他們靜靜地觀察熊蜂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至於大人嘛,我也沒有特別記得誰,或是有什麼難忘的回憶(當然還是有少數例外)。遇到那些已經見過很多次面的大人時,除非我爸媽提醒我對方養了哪些寵物,例如「他們家養了布蘭迪啊。」布蘭迪是一隻迷你長毛臘腸狗,牠的毛是紅色的,而且很喜歡依偎在我身邊。我上床睡覺時大人們還在開派對,布蘭迪就會過來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想不起來牠的主人叫什麼名字,也想不起來他們長什麼樣子,我通常會記得布蘭迪。我只會呆滯地看著對方,完全認不出來他們是誰。傑克叔叔(嚴格來說應該不是叔叔,而是傑克上校才對)是我父親的朋友,也是少數幾個沒有養寵物但我很喜歡的人。他會幫我畫身上有白斑花紋的小馬,他和我父親下西洋棋的時候,我會小心翼翼地替那些斑紋著色。
等我的語言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能開始描述事情後,我就在爸媽面前鄭重宣布:其實我是一匹馬。我繞著屋子狂奔,還不斷甩頭、發出嘶鳴聲;我父親同意叫我「小馬」,但我那個優雅、愛交際且對社會地位很有野心的母親希望她的寶貝女兒能有點判斷力,假裝自己是公主或仙女,因此她非常憂慮,擔心我是人家說的那種「智障」。
軍醫向她保證,「小馬」只是一個階段而已,一定會隨著時間過去。果然沒錯,後來我就不覺得自己是馬了───其實我是一隻狗。從我的角度來看,這種認知只顯示出一個問題。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急著教我該怎麼當個小女孩,卻沒有人告訴我該怎麼當一隻狗;一直到我三歲,也就是莫莉出現在我生活中那一年,我那短暫的人生目標才終於實現。
育種中心的網站上描述年幼的蘇格蘭㹴犬「個性大膽活潑,很有自信」,而且特別「任性、固執又好動」,獨立強悍的性格特質早在幼犬期便展露無遺。崇尚節儉的蘇格蘭人培育出這個古老的品種以保護牲畜不受野獸侵擾,因此說這些體型嬌小、毛髮黝黑的蘇格蘭㹴犬是高地上的戰士也不為過。牠們不但勇敢又強壯,力氣足以制伏狐狸和獾,而且非常聰明,不需仰賴主人就能自己獨立工作,智取野外的入侵者。站著的蘇格蘭㹴犬大概只有二十五公分高,體重也只有九公斤左右;美國作家和評論家桃樂絲帕克(Dorothy Parker)說,牠們「集小型犬的敏捷與大型犬的勇猛於一身,體格也出乎意料的健壯,大家都知道,對蘇格蘭㹴犬來說唯一致命的就是被車子輾過,就連車子本身也很清楚這是場硬仗。」年幼的蘇格蘭㹴犬就像坐擁天生神力、而且還有在吃類固醇的恐怖兩歲小孩一樣,具備幾近反常的生命韌性及不可毀滅性。
不過,雖然我和莫莉一起度過了童年時光,但年輕、強悍又好鬥的牠跟我完全相反。
我剛滿兩歲時發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當時我們全家一起從德國(我的出生地)搬回美國,我們在德國有請保母,搬回美國後就變成我母親負責照顧我。後來我才從她口中得知,我染上了非常罕見的幼兒單核白血球增多症(mononucleosis);可是我姑姑覺得根本沒這回事(的確,多年後我在自己的軍事醫療紀錄上完全找不到這項診斷結果),反倒認為可能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猛烈搖晃我的身體、把我悶住,或是兩種都有。當時我確實整天哭個不停,甚至好幾年後我都已經進入青春期了,我母親還是常常滿懷憤恨地跟朋友抱怨我的哭聲毀了她的雞尾酒時光。對她來說,一天之中最棒的部分就是晚上那幾杯馬丁尼。當我父親不在家,剩她孤身一人面對嚎啕大哭的寶寶時,這些酒精想必能減輕她的寂寞感吧。
不管我到底生了什麼病、遇上了什麼事,總之過了幾個月後我開始不玩,不講話,也不吃飯。到了三歲的時候,我還是非常瘦小,完全沒有長大。我爸媽很擔心我的身體狀況。我母親買了一個底部畫有動物圖案的小碗,這樣只要我把麥片吃完就能看到那些圖案;另外,她還會用餅乾模具把吐司切成動物的形狀,我父親則試著用奶昔(他都會偷偷地在奶昔裡加一顆生雞蛋)引誘我、哄我吃東西。眼看我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們心裡非常焦急,這股絕望感可能就是讓他們開始考慮領養狗狗的原因。
現在的馴犬師和親職教練應該會勸我爸媽不要這麼做。馴犬師認為蘇格蘭㹴犬的確是很棒的狗,但不太適合小小孩,因為嬰幼兒可能會踩到狗的腳或抓牠們的尾巴,蘇格蘭㹴犬不但不會容忍這種事,反而有很大的機率會咬人,牠們的下顎和牙齒就跟「㹴犬之王」萬能㹴一樣大,雖然異常忠心,但也是㹴犬中最兇猛的品種。目前大部分的專家都建議,就算是個性溫順又有耐心的犬種,還是等到孩子六、七歲再養比較好。
當然啦,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這些事,所以葛蕾絲阿姨(她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古巴女子,因社會及政治因素被迫移民、流亡海外)就從她養的三隻可愛狗狗裡選了一隻送給我們。
葛蕾絲阿姨並不是我真正的阿姨,而她先生,也就是我從小叫到大的克萊德叔叔也不是我真正的叔叔。克萊德叔叔是我父親最好的朋友,但葛蕾絲阿姨卻是我母親的假想敵。葛蕾絲阿姨穿著胸前開低衩的高級訂製窄裙洋裝,畫著黑色眼線,塗著緋紅色口紅,腳上踩著高跟鞋,一頭及腰的烏黑秀髮優雅地挽起,盤成華麗的髮髻。我母親覺得她很愛炫耀,有一次她問我:「妳猜葛蕾絲阿姨穿什麼顏色的洋裝帶狗狗去獸醫那裡打疫苗?」
「黑色嗎?」我猜。就我個人來說,我會很希望自己看起來盡量和其他家人一樣。「不是,」我母親立刻糾正我。「是白色!」這樣才能襯托狗狗本身的顏色。
我想莫莉應該是看完獸醫沒多久就來我們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分子。莫莉來的那天堪稱我短暫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可是───唉,可能是因為我的病、我受的傷,或是我年紀太小的關係吧,總之我對這個扭轉生命的關鍵時刻一點印象也沒有。
不過莫莉很快就發揮了牠的影響力,而且效果非常顯著。
牠剛來我們家沒多久,我爸媽就幫我們倆拍了一張黑白照片,我母親想在聖誕節,也就是我四歲生日前兩個月把這張照片做成節日賀卡寄給親朋好友。照片裡的我穿著澎澎的燈籠短袖服裝,壁爐上方掛著聖誕襪,聖誕老公公機器人則站在我旁邊的磚石地板上準備搖銅鈴。這張照片就和我母親做的所有聖誕賀卡一樣,從場景到構圖全都是刻意安排的,但我和莫莉流露出來的興奮卻非常真實,那是發自內心的快樂。
14.8*21*1.5
25 開
序言
01 探索世界的動機 莫莉
02 勇敢地向未知敞開胸懷 鴯鶓三兄弟
03 去愛生活給予的一切 克里斯多夫
04 發覺這世界充滿未知的美麗 克拉貝兒
05 聖誕節的祝福 白鼬
06 明白真正的恩典 黛絲
07 找回對生命的熱情 克里斯與黛絲二號
08 讓我有更多能力去愛 莎莉
09 世界蘊藏各種智慧 奧塔薇亞
10 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 瑟伯
照片集
致謝
延伸閱讀
莎伊・蒙哥馬利作品集


(建檔用)-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