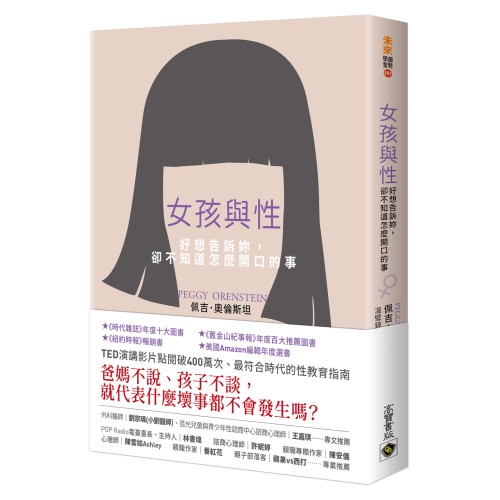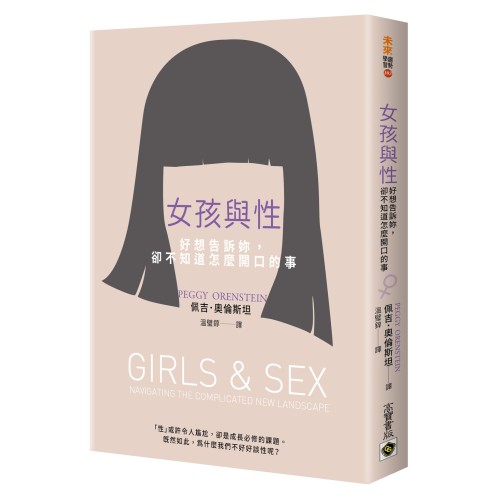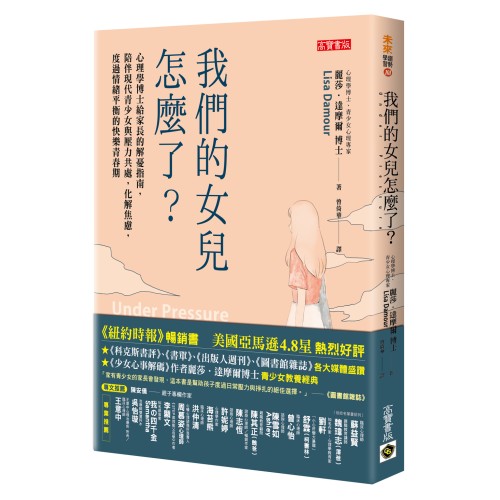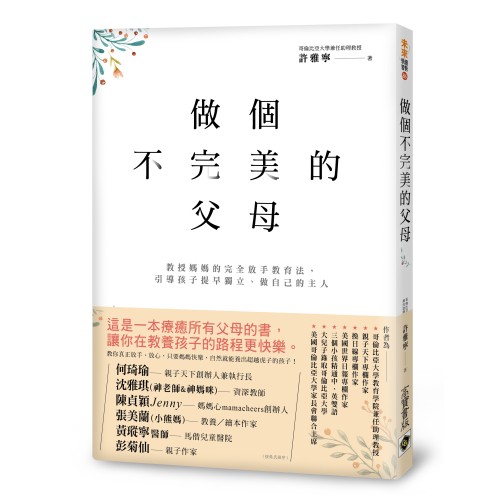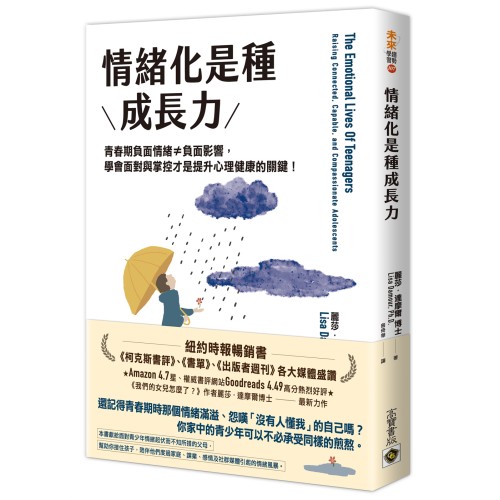會員限定
女孩與性:好想告訴妳,卻不知道怎麼開口的事
NT$300
NT$380
-
作者佩吉.奧倫斯坦(Peggy Orenstein)
-
譯者溫壁錞
-
ISBN9789865061043
-
上市時間2021-04-28
- 親子教育
-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爸媽不說、孩子不談,就代表什麼壞事都不會發生嗎?
TED演講影片點閱破400萬次、最符合當代的性教育指南!
如果不舒服,還能說「不」嗎?不想發生關係又該如何拒絕?
為了找出答案,本書作者佩吉.奧倫斯坦開始和許多15~20歲的青少女對話,也和心理學家、醫生、教育家、社會學家等專家交流。她發現──
其實,比起網路上真真假假的訊息,孩子更想和自己信任的大人討論對性與愛的想法。
即使現代的家長比以往更關心孩子,大部分還是不知道或不習慣跟孩子討論性,也不了解他們對性的看法與他們的性行為。
然而,近來已有許多研究發現,當大人越是不談、不教、不准,孩子越容易從網路、流行文化、朋友身上學到錯誤、偏頗的性知識,也可能因此無意中讓自己或別人陷入危險;相反地,如果父母能夠更坦率地分享,孩子反而不會亂來,也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這本書,將幫助爸媽面對自己的不自在,克服自己的成見,趕上孩子的進度,好好了解青少女的性是怎麼回事,成為彼此更好的盟友。
◎榮獲獎項
《時代雜誌》2016年度十大圖書
《舊金山紀事報》2016年度百大推薦圖書
《紐約時報》暢銷圖書
美國Amazon 2016年度編輯選書
美國Amazon 4.6星高分好評
Goodreads 4星熱烈迴響
◎專文推薦
外科醫師 劉宗瑀(小劉醫師)
芸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王嘉琪
◎專業推薦
POP Radio電臺臺長/主持人 林書煒
諮商心理師 許妮婷
親職專欄作家 陳安儀
心理師 陳雪如Ashley
親職作家 番紅花
親子部落客 蘋果vs西打
◎國外好評
「佩吉.奧倫斯坦說出了很重要且經常被誤解的話題。」──雪柔.桑德伯格,Facebook營運長、紐時暢銷書《挺身而進》作者
「書中所提出的,攸關我們女兒(噢,還有兒子)的情緒健康和安全。」──蘿瑟琳.魏斯曼(Rosalind Wiseman),美國知名育兒教育家、作家
「所有關心女孩、女人、人類的人必讀。我認真考慮辭掉工作,到全國瘋狂推銷這本書。」──拉什達.瓊斯(Rashida Jones),演員、製片人、作家
「如果你打算聊聊21世紀的女生,那你一定要讀這本書。」──凱特琳.莫倫(Caitlin Moran),《泰晤士報》記者
前言
小女生與性愛: 你從來不想知道(卻真的該問清楚)的事
幾年前我就知道,再過不了多久,女兒就不是小女孩了,她已邁向青春期,老實說,這讓我有點恐慌。遙想昔日她上小學之前,穿著灰姑娘的洋裝轉圈圈,這時我曾經深入研究公主產業情結,然後深信這種看似天真的粉紅美麗文化,日後會讓小女孩培養出某種更陰險的特質。好極了,當年的「日後」,現在就像一輛失速大貨車衝著我們來了──開車的穿著五吋高跟鞋和超級短裙,該仔細看路時,卻在刷著她的IG。朋友已經跟我說了不少青少年的恐怖故事,述說著女生怎樣被迫發送自己的不雅照片,怎樣因為社群媒體的醜聞而受害,A片又是如何地無所不在。
解構少女時代的混合型訊息,這方面我應該是專家。我巡迴全國,教父母親如何區分性化(sexualization)和性(sexuality)。我會告訴父母:「小女孩還不明白『性感』(sexy)的意義時,就在假裝性感,這時候她們所認知的性是一種表演,而不是一種感受經驗。」這話很真,但是萬一這些女孩子是真的懂得了「性感」的意義呢?
這個問題,我好像也沒有答案,因為我也只是在這樣的時代,竭盡心力,撫養一個健康的女兒。這個時代,很多名人,認為自我厭惡(self-objectification)是實力、權力、獨立的來源;「長得誘人」似乎等於感受慾望;《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中,神經衰弱咬著嘴唇的女主角,配上死纏爛打到令人毛骨聳然的億萬富豪男主角,卻被譽為極致女性奇幻故事;這個時代,四十歲以下的女人都剔陰毛。當然了,我自己的少女時代,是把「愛情祕方」(Sexual Healing)或「宛如處女」(Like a Virgin)之類的歌都唱爛了,然而,跟當代的某些歌曲比起來,那些僅只是迪士尼等級的素材而已。比如說,小韋恩(L´il Wayne)的歌曲「愛我」中,有個「婊子」,這婊子「嚴格控制的飲食」別無他物,只有「雞雞(dick)而已。又或如魔力紅在「動物」(Animals)這首歌的歌詞中,保證要獵捕一個女人,將她撲倒,生吞活剝。(影片中,樂團主唱亞當.李維扮成屠夫模樣,揮舞著肉鉤,跟蹤著自己迷戀的目標,然後在血淋淋的最終章時,與她交媾。)不說別的,光憑這一段,我就該為自己九○年代居然和朋友一起嘲笑過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蒂珀.高爾而鞠躬道歉。此外,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也顯示性侵害案件在大學校園裡氾濫得驚人,問題之嚴重,就算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本身也是兩個青春期少女的父親)也不能置身事外。
即便當年大學裡女生人數比男生多,這些女孩「挺身而進」要完成自己的學術與專業夢想時,我還是不得不懷疑:我們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現在的年輕女性,打造自己的性接觸經驗時,是比她們的母親更自由,更有影響力,也更能掌控嗎?她們是否更能抵抗汙名,更有備而來的探索性的愉悅?如若不然,又是為什麼?現在女孩生活的世界,有一種文化,這個文化越來越講究「除非雙方都明確同意性接觸,否則就等於不同意」──只有「可以就是可以」,非常好,可是,「可以」之後呢?
我身為人母,也是記者,需要找出標題後面的真相,釐清何為真、何為假設。於是我開始找女孩們談:廣泛地針對身體親密接觸的問題,進行幾小時的深度訪談,瞭解她們的態度、期望以及早期的經驗。我找遍了朋友的朋友的女兒(還有這些女孩們的朋友,當然還有她們朋友的朋友),也訪談了我認識的高中老師的學生。當年我也要求拜訪過的大學教授廣發電子郵件,邀請所有有興趣跟我約談的女孩們碰個面。最後,我訪談了超過七十個年輕女性,年齡介於十五到二十歲,這個年齡層的女孩,大部分都開始有性經驗了。(美國人第一次性經驗的平均年齡是十七歲;到了十九歲時,已經有四分之三的青少年都有過性經驗)。我主要的重點還是只放在女生身上,因為身為記者的我,為年輕女性而寫,已經是我的熱情所在,是上天的感召:畢竟我已經用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為她們寫生命編年史了。女孩們也一樣,在進行性方面的選擇時,繼續與獨特的衝突共存:雖然在期望與機會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女孩們仍然受制於和以往相同的雙重標準,亦即「性活躍的女生是蕩婦,而同樣性活躍的男生卻是玩咖」的概念。此外,放棄性愛的女孩,過去被認為是「乖女孩」,現在則被貼上「處女」(這不是什麼好事)或是「假正經」的標籤,因而仍然感到羞愧。誠如某位高中生跟我說的:「通常負面的相反就是正面,但這件事情卻都是負面。所以你又該怎麼辦?」
我不敢說自己能反映所有年輕女性的經驗。我訪談的對象,不是大學生,就是計畫要上大學的──某些女生覺得自己的人生有種種可能,某些女生已經受到女性的政治/經濟地位提昇而受益,我很希望跟這樣的女性訪談。接受約談者,是女孩們自己的選擇。話雖如此,我撒網的範圍還是很大,遇到的女孩來自全美各地,大城市和小鄉鎮都有,有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徒、福音教派信徒、猶太教徒,甚至是非特定宗教派別的信徒。有些女孩子的父母有婚姻,有些則是離異,有些住在離婚又再婚的重組家庭,有些來自單親家庭。政治上,有保守派的,也有傾向自由派的,不過大多是自由派的。受訪的女孩多為白人,但也有不少亞裔、拉丁裔、非裔美國人或混血種族。受訪的女孩當中,大約有百分之十認為自己是女同志或雙性戀,不過大都還未能在別的女生身上發揮自身的吸引力,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女孩子。受訪的女孩有兩位是身障。受訪者多半來自中上階層的家庭,但所屬的經濟條件也有落差──有來自曼哈頓東區和芝加哥南區的女孩;也有家中父母在操作避險基金或開速食餐飲的。為了保護她們的隱私,我用了化名,也改了能夠顯露她們特徵的細節。
一開始我擔心這些女孩子不願意跟我討論如此私人的話題。如今想起來我當初真是多慮了。訪談的時候,無論我到哪裡去,總有許多的女孩志願來受訪,人數多到讓我應付不來。她們不只是積極,根本是衝過來跟我談。在遇到我之前,從來沒有大人問過她們性方面的經驗:沒有人問她們做了什麼、為什麼做、感覺如何、希望怎樣,也沒有大人問過她們後悔什麼,哪一點好玩。通常訪談的時候,我幾乎問不到一個問題,這些女生就會自己開始說,不知不覺之間,好幾個鐘頭就過去了。她們告訴我自慰、口交(無論是幫對方,還是對方幫自己)、性高潮是什麼感覺;她們說起自己怎樣遊走在處女與蕩婦之間;還說起某些男孩有野性,而某些男孩很溫柔;某些男孩會虐待她們,某些男孩卻能夠讓她們恢復對愛的信心。她們承認自己有魅力迷倒其他的女孩,卻又害怕父母反對。她們談起勾搭文化(hookup culture)的複雜面,勾搭文化裡,偶然的接觸先於感情連結(而且也許會有感情連結,也許不會有);勾搭文化在目前的大學校園很普遍,也正迅速地蔓延到高中。一半的女孩曾經體驗過介於強迫到強暴之間的各種狀況。那些故事令人聞之心痛,但同樣令人難過的是,這一半的女孩,只有兩個人曾經向別的大人述說過自己發生的事。
而即使是雙方都同意的性接觸,這些女孩所描述的內容,聽來仍令人心碎。或許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本身卻值得探討。雖說公開領域裡,對女性的待遇已經有這麼大的改變了,為什麼在私領域裡卻不能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改變呢?如果房間裡沒有平等,那麼教室和會議室裡,會有真正的平等嗎?回顧一九九五年,美國國家青少年性健康委員會宣稱健康的性發展是基本人權,還說青少年的親密關係,應該是「雙方同意、非剝削、坦誠,愉悅的,並且是保護青少年免於非預期懷孕與性傳染病的。」結果二十年過去了,我們落後這個目標這麼多,到底是怎麼回事?
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莎拉.麥克利蘭(Sara McClelland)曾經寫文章指出,性是一種「親密正義」,文中探討最個人的關係中,充斥的性別不平等、經濟不平等、暴力、身體尊嚴、身心健康、自我效能、權力動態等基本議題。她要我們考量:誰有權利投入性行為?誰有權享受性行為?誰是性經驗最主要的受益者?誰覺得值得?當事雙方如何定義什麼叫做「夠好」?細看各年齡女生的性時,這些問題很尖銳,尤其當我們在看小女生早期、形成期的性經驗時,更是如此。雖然如此,我還是決心要深入這些問題。
我訪談過的女孩們,在訪談結束很久之後,有不少仍然與我保持聯絡,發電子郵件來報告新的感情狀況,或者述說自己發展出的信念。第一個寫道:「我想讓您知道,因為跟您談過話,所以我轉系了。我要改唸保健,專攻性別和性。」第二個,是國中生,她告訴我,受到我們的討論影響,她去大學校園參訪時提出了不同的問題。第三位就讀高三,她直接向男朋友坦承她所有的「性高潮」都是裝的;不過另一個高中女生卻告訴她的男友不要再逼她達到高潮,因為這樣會毀了性愛。這些訪談──無論對象是年輕女性本身,還是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兒科醫生、教育人員、記者或其他的專家──也改變了我,迫使我面對自己的成見,克服自己的不自在,釐清自己的價值。我相信那樣的改變,已經讓我成為更好的母親,更好的阿姨,成為我生命中年輕的男性及女性更好的盟友。希望看過這本書之後,您也會有同感。
14.8×21
25 開
推薦序 拉近親子間的距離
推薦序 幫助孩子有能力去釐清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前 言 小女生與性愛:你從來不想知道(卻真的該問清楚)的事
第一章 瑪蒂達不是物品──除非她自己願意
第二章 我們玩得開心嗎?
第三章 宛如處女,管它是什麼
第四章 勾搭與感情障礙
第五章 出櫃: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第六章 模糊界線: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七章 要是我們把真相告訴她們呢?
致謝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