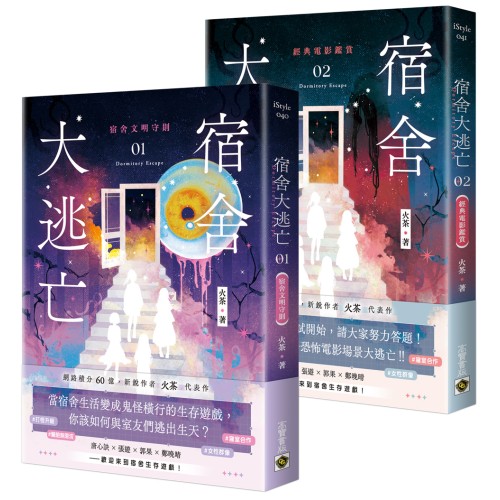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喜愛《深夜小狗神祕習題》的讀者,絕不能錯過此書!
「這本小說太棒了……有懸疑又有娛樂性,你一定會喜歡這本小說!」——史蒂芬・金
★「愛倫坡獎」年度最佳小說大獎提名
★《書單》星級書評
★亞馬遜最佳推理、驚悚與懸疑圖書
謝天謝地,我的生活一點也不驚險刺激──我原以為如此。
從目睹綁架的那天起,我的人生瞬間從無聊的紀錄片變成驚悚懸疑動作片。
不過,總而言之,我還沒死。這是好事!
*
身為幾乎全身癱瘓的肌肉萎縮症患者,我偏好默默觀察世界,你懂的。
那個女孩每天固定時間經過我家,直到那一天──她上了那個詭異男子的車。她從此消失了。
*
丹尼爾在喬治亞大學城過著平凡而滿足的生活。他有幾個親密的好友,時常一起在家閒聊鬼混。他在航空公司擔任線上客服,有穩定的薪水。每一年秋天,他都會和朋友一起參加美式足球賽季盛事。
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無比幸運。即使他無法說話、全身上下只剩手指和腳趾能靈活活動、得靠輪椅才能去任何地方,而且每天都可能被自己的痰噎死。
這些都阻擋不了丹尼爾享受人生。只要天氣晴朗,他都會到家門外的前廊親眼感受這個世界。
有一位女大學生每天都分秒不差在同一時間路過丹尼爾家,觀察這個女大生已經成為丹尼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這一天,規律的生活被打亂了。女大生失蹤了。
丹尼爾幾乎可以肯定他目擊到女大生被綁架的過程。他開始收到一封封詭異郵件,而寄件人,就是唯一的嫌疑犯……
【好評盛讚】
「有什麼比一個虛構的角色用我們以前從未聽過的聲音對我們說話更令人興奮?尤其是如此真實又直接的聲音⋯⋯Will Leitch這本聰明、有趣、又令人心碎的小說《How Lucky》的主人公Daniel,就是這樣一個聲音。我不確定在本書結束後,它會不會完全離開我的腦海,或者我希不希望它消失。」——理查・羅素
「有趣、淒美且引人入勝的真實寫照,本書清晰描繪了被困在一具軀體裡的感覺,是本優秀的作品。」——亞馬遜網站編輯Vannessa Cronin
【讀者迴響】
「懸疑和笑聲之間取得絕妙平衡!」
「敘事輕鬆幽默,也充滿了溫暖。」
序章
我的人生不是一部驚險刺激的電影。我的人生正好是驚險刺激的相反。真是鬆了一口氣。誰希望自己的人生那麼刺激啊?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精彩──我們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激勵人心、能充滿驚喜,能在每天早晨都給我們一個起床並體驗新事物的理由。但是刺激呢?別開玩笑了,老兄。所有在冒險電影裡發生的事件,如果發生在現實生活,那都會他媽的嚇死人。你在電影裡看過成千上萬的飛車追逐,次數已經多到當你邊摺衣服邊看網飛時,飛車追逐的鏡頭甚至讓你連頭都懶得抬起來的程度。你都已經看膩了;那些畫面千篇一律又無聊。但如果你身處其中一場追逐戰裡,那就是一場惡夢了。你的奔跑就會是為了……逃命!如果你活下來了,你也要花好幾年的時間試著走出來。你在做心理諮商的時候會發抖又畏縮,你會一次又一次地在惡夢裡重新經歷這一切,然後再尖叫著醒來,你會再也沒辦法和其他人建立起人與人的連結。這會是發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一件事。
謝天謝地,現實生活並不驚險刺激。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你身上,也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的人生只是由一堆小小的片段時光所組成,你的也是。我們不會生活在一連串的劇情轉折裡。我們應該為此心懷感激。我們應該要慶幸自己有多麼幸運。
*
當我說我看見她爬上那台大黃蜂時是早上七點二十二分,請相信我,我很確定時間。因為我一直都很有規律。你也許不這麼認為,但我的規律和你的其實也相去不遠。我很確定,因為那天只是個普通、平庸的早晨,就和任何其他日子一樣。我很確定,因為我就像往常一樣看見她了。
瑪扎妮早上六點叫醒我。我們靜靜地吃了一頓早餐。我回覆了幾封電子郵件,滑了一下IG,直到《今日秀》開播,將前一晚全世界發生的恐怖事件都攤在我面前。歐塔愉快地描述完世界是如何分崩離析後,艾爾告訴我們,今天拉斯克魯塞斯的氣溫會高達攝氏四十一度,喔耶,然後他咧開嘴,把畫面還給了《十一點新聞直播》,那是亞特蘭大的當地電視台。此時一如每個平日,都是早上七點十七分。然後就到了「威氏量表」的時刻。威氏量表只是一個數字,介於一到十一之間,為這個星球當天的氣候做評分。十一代表的是最理想的天氣,而我猜一則代表當天會下一場讓世界滅絕的流星雨。柴斯利.麥克尼爾會用整整四分鐘的時間告訴我們當地的天氣狀況,然後在把鏡頭切回去給位於紐約的艾爾之前給出威氏量表評分。
那四分鐘有時候真的讓人很痛苦。我的情緒狀態有時候會被威氏量表嚴重影響,這一點其實滿令人擔心的。我在家工作。我一直都在家裡。「外面」指的是我的前廊以外的地方,而我只有很少很少的機會能到外面去。威氏量表能讓我擁有看看外頭世界幾分鐘的邀請函。如果威氏量表給出了八分,就像今天這樣(「亞特蘭大,好好期待你們的週末吧!」),我就要盡快離開家門,趕到前廊上。更準確地說:我會在七點二十一分移動出家門。今天是這樣,明天也會是,只要我還有辦法出門、只要氣象預報是好天氣,我就會這麼做。
瑪扎妮走向自己的本田小轎車,對我揮手道別,明天見啦,丹尼爾。我們的規律現在已經成了一支無聲的舞蹈,是由多年來的經驗累積而成,瑪扎妮是弗雷德.亞斯泰爾,我則是琴吉.羅傑絲,照著她的動作移動,只是和她順相反、還穿著高跟鞋。她的英文現在很好了,但在過去幾年她還不太會說英文的日子中,我們學會了這支沉默的探戈之舞。有時候我們會聊聊。有時候不會。我看著她的老車低吟了一聲又一聲,才終於啟動。從我認識她的時候開始,她就在開這輛車了,我真不知道它怎麼還跑得動。
瑪扎妮駛過農業路,前往史第格曼體育館。前一晚的體育俱樂部活動結束後,她要去幫忙清潔現場。有一場喬治亞大學的主場美式足球賽要開打了,意味著這一週會充斥著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也意味著瑪扎妮會有更多工作。她早上會先來照顧我,然後接著去做一連串奇怪的工作,例如打掃、褓母、居家拜訪、有時候也會幫忙掌廚。她昨天是這樣過的,接下來的幾百個明天也會是這樣。如果那輛有氣無力的車還能動的話。
我用吸管喝了一口水,在前廊上看著她離開。一個背著「水土不服樂團」背包的小孩心不在焉地走到大街上,使瑪扎妮不得不踩下煞車;孩子舉起手,半是道歉、半是漫不經心的習慣動作,然後走進了樹林裡。除此之外,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當整個雅典的人都在宿醉時,早晨就是這麼寧靜。所有人好像都決定多睡一個小時似的。就連平常擠滿謹守本分的博士生的學生家庭式宿舍,現在也昏昏沉沉,光線昏暗。我深吸一口氣,享受外頭難得的寧靜時光。要只有我一個人在屋外,這機率能有多大?我一個人能有多少這樣在外獨處的機會?
然後我就看到她了。我現在描述給你聽時,把它講得很戲劇化,好像她突然跳到我面前一樣,好像我根本不可能沒看到她,好像她在一個黑白世界中穿著一件大紅色的外套一樣。好像我在一部驚悚電影裡一樣。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她只是像平常一樣走著路。通常不只有她一個人會大清早在路上走,但在那天,就只有她一人。過去三週,我每天都在這個時間點看到她,分秒不差。也許她是個大二學生,她背著一個藍色背包,走在人行道上,和瑪扎妮剛才開車行駛的方向相同。今天是個美好的秋日,威氏量表八分、也許九分,此時是早晨七點二十二分,她正漫步走過農業路,輕鬆寫意,只是另一個準備走去上課的孩子。
一如往常,她和其他人只有一個地方不同,就是她沒有戴耳機。她從來不戴耳機。她不抬頭、總是獨自一人,她會融入人行道的街景。她從來沒有看見我坐在這裡,坦白說,如果不是她每天都和我在同一個時間出現在外面,我大概也不會注意到她。她就只是走路。她不會做別的事。
直到那一天。那一天,她停下了腳步一秒鐘。沒有任何原因:沒有車突然停在她面前、使她需要繞道之類的。她只是停下腳步,抬起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我視線相交。那顯然是個意外;她的視線挪開的速度比落在我身上的速度還快。但她看見我了。我也看見她了。她又停下腳步,再度瞥了我一眼,這次更仔細了一點,然後露出淺淺的微笑。她舉起右手。哈囉。然後她又繼續走她的路。
一輛大黃蜂左轉,從南景路駛上農業路。這輛大黃蜂已經變成了黃褐色,需要重新烤漆,而且需要比現在更悉心的照料。我猜那是六○年代末的復古車款——那時候的大黃蜂還被人視為高級的跑車,而不是七○年代的莎莉或貝蒂搶著要擠上車的炫耀工具。這輛車值得你投注大量心血,使它恢復昔日榮光,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疏於呵護。
車子在她身邊停了下來。她看向車內。她似乎聳了聳肩。她搖搖頭,似乎笑了一聲,然後又聳聳肩。駕駛接著便打開了副駕駛座的車門。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我注意到兩樣東西:我瞥見了他左腳閃亮、近乎半透明的靴子尖端——像金屬一樣會發光——還有他頭頂上戴著一頂藍色的亞特蘭大鶇鳥隊帽子。我記得,就連在那一刻,我都覺得那頂鶇鳥隊的帽子很奇怪。十到十五年前,確實有一支冰上曲棍球隊叫作亞特蘭大鶇鳥隊,但南方根本沒有人喜歡冰上曲棍球,所以他們就遷到加拿大的溫尼伯去了。誰會戴亞特蘭大鶇鳥隊的帽子啊?
她頓了頓,微微向右看了看,好像在確保沒有人看到她。然後她往左看過來,又一次看到了我。她很快地撇開視線,好像有點難為情,又或者只是在尋找著什麼,好像在尋求……什麼?我的同意嗎?也許她只是很高興有人在看她。也許她是希望沒人看到她。我不知道。那只是一個尋常的秋日早晨。我沒有理由多想這件事,所以我沒有去想。你也不會多想的。這只是件小事。
但她確實是上了那輛車。那是早上七點二十二分。我很確定。
***
星期二
1.
十一點十三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一個陌生人稱為「混蛋殭屍實習生」,而且老實說,對死氣沉沉的星期二而言,這還不算太糟。週二到週四的旅客通常都是商務旅客,他們通常比觀光客好一點,但當事情出差錯時,他們又比觀光客更氣急敗壞,因為他們有地位。但今天是個輕鬆的星期二,威氏量表的數字很漂亮,這一定使大家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我猜「混蛋殭屍實習生」分別指的是我整體而言令人噁心、毫無靈魂、又對社會沒有任何影響力的狀態。(第一個詞太殘酷、也太荒唐,我們甚至不用認真討論我的性向究竟是或不是什麼。)使對方抓狂的意外是一場小暴風雨,那是我唯一能從即時氣象預報軟體中能看見的暴風雨,而它顯然使@pigsooeyhogs11去納什維爾要搭的那班飛機被困在阿肯薩斯州的小石頭郡了。雖然我可以同理他被困在阿肯薩斯州的不幸遭遇,但我也幫不上什麼忙,因為我正坐在喬治亞州雅典市的一張桌子前。但他不希望我幫忙。他只想要我坐著聽他發飆。我擁有做這份工作的獨特技能,而坐著聽他發飆就是其中一項。
@spectrumair 在機場裡坐了二十五分鐘了 沒有任何消息 三小啊?
@spectrumair 三十五分鐘了 還在等 #去你的光譜航空
@spectrumair 我知道你不在乎 但我還在等
公司訓練我們不要逐條回覆訊息。其實也不是辦不到——光譜航空是個地區性的小航空公司,只會來回八個機場、一天只飛三次;就算每個乘客都抓狂,我們也不會忙不過來——但逐條訊息回覆,會讓他們產生一個錯覺,好像我們真的在乎他們的抱怨一樣,但其實我們並不在乎。當然,我們得看起來像是在乎:就算只是一個總部設立在阿拉巴馬州的小航空公司,他們也不希望自己看起來像不重視自己忠實的顧客。但他們真的不在乎。如果他們真的在乎,他們就會花錢聘請全職的公關團隊和一個社群網站協調專員,或者,也許可以買幾架不會被幾片八十公里以外的小烏雲困住的飛機。但光譜航空不是這種公司。光譜航空只會花時薪二十五美元,聘請我溫和地回覆那些「不滿意」的推特發文。不過你只花七十九元,買一張從小石頭飛往納什維爾的單程機票,一分錢一分貨嘛。
當然,我可不是這麼告訴他的。在他發了三條推特,我則從總公司那裡得到警示,說航班在「天氣狀況緩解」前將無限期停飛之後,我才回覆。我得用比別人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回覆大家的訊息,我猜這也是他們喜歡讓我做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pigsooeyhogs11 很抱歉造成您的不便。您的航班受到天候影響,此時我們還無法提供您更多資訊,但有任何更近一步的消息,我們都會立即通知您。
一定要記得在回覆生氣的顧客時加上「等我電話」的表情符號。你能對一個表情符號發多大的脾氣?如果我們能單靠表情符號溝通,這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了。
事實證明,@pigsooeyhogs11可以對表情符號發很大的脾氣:又過了兩條推特的時間後,那句「混蛋殭屍實習生」就出現了。一旦顧客開始口出穢言或是暴力相向,我們就無計可施了,所以公司叫我們直接在推特上把他們消音。你不能封鎖他們——那會讓他們知道你其實聽到抱怨了——公司的指示是,把他們消音就好,把他們所有的尖聲大叫和抱怨連連全部丟到外太空去。讓他們對著一片混沌大吼大叫就好了。
我得承認,生氣的人們在手機上打出各種羞辱人的話,卻沒有人會看到,因為他們被消音了,這件事就某種層面上來說,其實有它的正面意義。以這種角度看來,我的工作幾乎是一種公共服務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惡魔要應付,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很難找到地方發洩所有的挫敗感。你可以對著枕頭大叫,或者對你的狗發飆,或者讓這些挫折感持續堆積,直到在錯誤的時機點爆發,進而傷害到你自己或你在乎的人。我必須說,在網路上對廉價地區航空表達憤怒,其實是最有建設性也最健康的方式之一。反正人們需要找地方發洩情緒。對我們發洩情緒也沒什麼不好。
但話說回來,我從來沒有把他們消音。現在他們是憤怒的旅客,但在飛機之外,他們只是別人的兒子、女兒、媽媽、爸爸、同事和老闆,他們只是在超市排隊的第五個顧客或去醫院探病的焦慮親屬,而最後,他們只是躺在棺材裡的一具軀體,讓許多坐在折疊椅上的人後悔自己沒有花更多時間陪伴而已。他們正在經歷痛苦,迫切地需要人們聽見他們的聲音,而剝奪他們這個權利似乎有點太吝嗇了。他丟出「混蛋」這個詞之後,對話就結束了。但要我叫某個痛苦的人閉嘴,實在太殘酷。公司政策是要我們把他們消音。但我就是做不到。
當有人越界,而公司政策明文規定我不能再和對方互動後,我很喜歡做一件事:我會去找和他搭同一班飛機、但用比較溫和的方式抱怨的其他旅客,然後給他們更多資訊。也許他們就坐在那個生氣的人附近,他們就可以告訴他了。至少我想這麼相信。我喜歡想像,和那個叫我混蛋的人搭同一班飛機的陌生人,得知飛機會在二十分鐘內起飛後,會去告訴他。那個生氣的人會放下手機,忘記自己一開始還在發脾氣,露出微笑,然後說:「噢,謝謝你。」好心人則會回應他的微笑。兩個陌生人以愉快的方式交換資訊,兩人都成了對方今天的亮點,這件事雖小卻事關重大,使兩人的日子都好過了一點。我們每天都會有這種互動。當有人幫我們開門的時候。排隊時有人替你揀起掉落的眼鏡時。沒有人會記得這些寧靜、迅速又平庸的善意小動作。我們只會記得那個在推特上叫我混蛋的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其實很親切,就算只是無意義的善意也一樣。船過水無痕。但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在網路上總是比在現實生活中憤怒得多。
我做這份工作的表現要不就是堪稱完美,要不就是爛透了。我還不確定是哪種。但這是一份工作,而老實說,願意雇用我的公司應該也沒幾間了。所以我絕不會抱怨這份工作。就算@pigsooeyhogs11說他希望得腦癌、然後在大火中死掉也一樣。仔細想想,我其實不確定腦癌會不會使被火燒死這件事變得更痛苦或更致命。
門鈴響起,而我一如往常地花了好多時間上網,我甚至沒注意到整個早上的時間都過去了。我登出帳號,前往大門。崔維斯會來進行每週二的午餐拜訪,這次他帶了巴赫餐館的烤肉三明治。我已經忘了@pigsooeyhogs11和那天早上我和其他人所有的互動。大腦的運作方式也是滿有趣的。
21*14.8*1.55
25 開
序章
星期二
1.
3.
4.
5.
6.
7.
星期三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星期四
18.
19.
21.
22.
23.
24.
27.
28.
29.
星期五
30.
31.
32.
33.
34.
35.
星期六
36.
37.
38.
39.
40.
41.
星期天
42.
43.
44.
46.
48.
星期一
49.
51.
52.
53.
54.
56.
57.
58.
59.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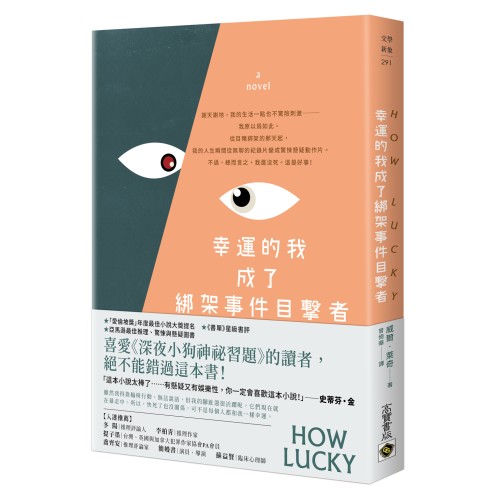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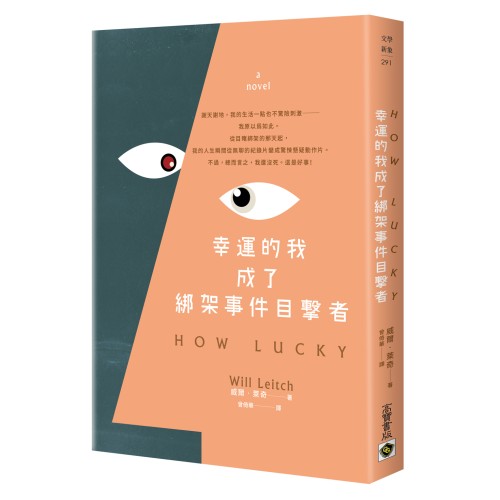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20腰_立體書-500x500.jpg)
(二)-套書-500x500.jpg)

印簽_立體書-建檔更新-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