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你願意為這人間至味,冒多大的風險?」
★古風幻想派人氣作家殷羽奇幻大作,盛宴再現!
★同名影劇即將盛大開播!
王佑碩、安悅溪 領銜主演
阿里影業出品,《舌尖上的中國》團隊拍攝劇中美食
自古只聞妖獸吃人,何時見過妖物淪為盤中佳餚?
一間食府天香樓,一隻化身少女的神獸饕餮,端上人與妖獸七情六慾熬出的滋味。
▋《饕餮記【第一部】(上)》
無夏城蓮心佛塔前,座落盛名遠揚的食府天香樓,門口高掛寫著朱字的白紙燈籠。
千年妖獸饕餮朱成碧為了守住承諾,五百年來守護無夏安寧,一邊化身神祕莫測的少女掌櫃,烹製迷醉人心的絕世佳餚。
人類與妖獸皆登門請託,獻上有愛情添味的活鮫人、能修改命格的虎妖掌、令人不惜烈焰焚身仍要貪食的朱雀蛋……
朱成碧以奇珍異獸入料,以愛恨情仇入味,嘗世間甘甜肥美滋味,品浮生腥苦酸澀人心。
為了這人間至味,人與妖甘願冒多大的風險?
▋《饕餮記【第一部】(下)》
☆獨家收錄!萬字番外〈天香簿〉
常青通曉獸語,妙筆生花,下筆成真,因欠了朱成碧三百兩銀子,成了天香樓帳房。
如今跟了朱成碧八年,即使不必賣身,常青也甘願留在她身旁。
凡人卻不如饕餮壽命千秋萬載,朱成碧出行尋覓能改寫人妖殊途的食材雙生菇,覬覦此菇的卻不只她一人。
此後無夏怪事連連,蓮池一夜乾涸,地穴憑空出現,各種罕見珍獸盡皆現身卻已成屍體,戴著木製面具的「半面鬼」陰魂不散。
這一切,卻是奉琅琊王趙珩所命,只為熬成那道菜餚,從此永保容顏,與天地同壽……
第一章 鮫人鱠
零
一抬頭,便看見了蓮心塔。
石質佛塔共有七層,六道棱邊,從上到下不見一絲接縫,連同蓮花形狀的底座,都像是由同一塊巨石雕刻而成。每一處飛簷下面都掛著一隻蓮花形狀的風鈴。整座佛塔都浸在夏末明晃晃的陽光裡,卻安靜得彷彿是浸在透明的冰水中一般,讓高琮不由得打了個寒顫,低頭縮脖,招呼身後四個扛著一隻青花大甕的苦力再走快一點。
望見佛塔時,可遇天香樓。給他指路的人果然沒有說錯,高琮停下腳步,給苦力們打了個手勢。在他們面前是覆著青瓦的三層木樓,一層臨街,大門緊閉,旁邊的烏木窗格上雕著團雲和仙鶴,二樓的圓窗正對著蓮心塔,窗櫺上沒有按照常規雕著八仙或者瑞獸,反而是雕著兩枝盛開的重瓣山桃。一位披著石青色直裰的少年背對著他們蹲在窗臺上,手持狼毫朱筆,正在給桃花上色。
他將筆懸在半空,凝神思考,喃喃自語,忽然落下一筆,再緩緩地將筆提起來。一瞬間,所有木刻的桃花都豐滿起來,旋轉著打開花瓣,再顫動著一片片凋落。
高琮驚得往後退了半步,但眨眼間,幻覺便消失了,留在原地的是實打實的木雕山桃,只是多了些灼灼的顏色。襯著一旁的月白色暗金盤紋厚絹窗簾,越發顯得鮮豔無比。
「落筆如生,常青公子果真好畫技——」
「天香樓今日不營業。」那人連頭都沒有回,低頭在一隻小碟裡蘸朱砂:「朱姑娘外出取材了。」
高琮咬牙。
「但是朱字燈籠還掛在二樓。」
天香樓沒有掛牌匾,只挑著只斗大的、寫著朱字的圓形白紙燈籠。如果有誰能有天大的面子,在自家府裡待客的時候請得動朱姑娘出馬,這燈籠就會高掛在這家的門口,而每一次,這家門口都會被圍觀的民眾擠得水泄不通。
「啊——」常青毫不羞愧地改口:「她還在午睡,況且,你也看見了,月白色窗簾也掛在二樓。」
月白色窗簾意味著天香樓的朱姑娘「心情不好」,而她心情不好則意味著所有來天香樓的食客都只能吃閉門羹。採取如此古怪的經營方式而竟然還沒有倒閉,唯一的原因是朱姑娘的廚藝過於驚豔,足以有恃無恐。如果高琮是個普通的食客,他大可就此回頭,等天香樓的二樓掛出繡了桃花的薄絹窗簾了再來。
但他不是。
「不過,這一次,月白色窗簾掛出的時間未免太長了些?據小生看來,足足有一旬?」
常青總算是轉過頭,用眼角打量著他,似乎還翕動了兩下鼻翼。
「小生聽說了一些傳言。」
「什麼傳言?」
「天香樓的朱姑娘苦於沒有少見的新鮮食材,而無法下廚。」
高琮把手探到懷裡,捏住一枚魚尾形狀的玉玦,緊緊地攥在手心。今天早上,這枚玉玦還藏在阿姣的枕頭下面,是她的至寶,此刻他渾渾噩噩地握著牠,彷彿還能感覺到她的體溫。他定了定心魂,朝常青舉起手中的玉玦。
「在下這裡,正好有一味世間少有的珍稀食材,想要獻給朱姑娘品鑑。若常兄願意代為引薦,感激不盡,願以此玨相贈。」
他一揖到底。這是明目張膽的賄賂,但常青與朱成碧不同,就高琮探聽得知,他欠了天香樓三百兩銀子,不得已才賣身給朱姑娘。這至少意味著,常青非常地,缺錢。
這世上,萬物都有價錢,只看你是否付得起。
一截繡著柳枝的腰帶晃動著出現在他視野裡,他一抬頭,那清秀的少年公子就站在跟前,笑得瞇縫了兩眼,一面伸著手,像是要扶他的樣子,卻巧妙地沒有碰到他的衣袖。他本就生得俊俏,這樣一來,更是讓人如沐春風。高琮只覺得指尖一鬆,玉玦就已經到了他的手上。
「何必如此客氣。」常青從袖子裡抽出一塊手絹,將玉玦擦了又擦,又對著陽光看了看成色。
「剛才居然忘記自我介紹,真是失禮。不才乃揚州『湯包常』第十七代傳人,現忝居天香樓帳房兼跑堂,這位公子,幸會了。」
他動了動手腕,玉玦就此消失在他的袖子裡。
一
雖說時日是夏末,天香樓的一樓廳堂內依然透著股子沁人心脾的涼氣,還混合著隱約的薰香。高琮跟在常青後面,踏上了通向二樓的樓梯。四個苦力扛著沉重的大甕亦步亦趨,水曲柳木的樓板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就在這時,一聲女子的呻吟如一縷柳絮,從他們頭頂飄落:「好餓啊——」
這聲音嬌媚無比,令人魂魄頓失。高琮腳下一個不穩,差點踩空,身後的苦力們被他這麼一阻,腳步紛紛趔趄起來,險些打翻大甕,連帶著潑出不少甕中之水。難以抑制的海腥味四散而出。高琮狼狽地重新站好,恨恨地瞪了苦力們一眼,又回過頭去瞥常青的臉色。他倒是面色如常,彷彿毫無察覺般繼續往上走,到了樓梯頂端才忽然轉身:「附加說明一下,整座天香樓所有的地板、樓梯還有欄杆,也都是由不才一個人刷洗的。」
高琮趕緊伸出袖子擦了擦欄杆,卻聽見他慢騰騰地補充:「算了,不用擦了。」
「公子寬宏大量......」
「反正你們走了之後我會把上上下下全部重新再擦洗一遍的。」
常青逕自推開旁邊一扇門就走了進去,從裡面傳來的薰香味越發強烈了。高琮自幼錦衣玉食,對薰香並不陌生,但卻無從分辨,只覺得一時如芙蓉花,一時又如龍井茶,一時卻如新出爐的糕餅一般,一層層紛至遝來,竟引得他腹中隱約「咕嚕」一聲。
「好餓啊......」
嬌媚的女聲沿著高琮的脊樑而下,彷彿無數雙撫摸的手。他不由得汗毛直豎,朝門內探了探身。他在樓下時望見的那扇掛月白色窗簾的圓窗就在眼前,只要一掀開,便能望見蓮心塔。室內的地面裝飾著軟墊,上面隨意甩著四五隻紅漆燙金的食盒,其中一隻的蓋子跌落,露出裡面毛茸茸的兔子形狀的糕餅。整整三排的形狀奇特的器具繫著紅繩,分門別類地掛在對面的牆上,其中的一半都是各式各樣的刀,在暗中幽幽地生著光。一道半透明的紗簾隔開了整個房間,其上浮動著手繡的桃花。
那嬌媚的女聲就是從簾幕內部傳來的。
常青站在簾幕前面,幾乎是敷衍性地略微拱手,便直起身來不慌不忙地回答。
「餓了就吃。」
「沒有東西可吃!我要餓死了,湯包——」
常青朝被扔在地上的兔子餅偏了偏頭。
「這可是尋芳齋的玫瑰酥,一日內只售十二隻,要賣一兩銀子一個。」
提到銀子兩個字的時候,他隱隱磨牙。
「你們都被騙了!做餡兒用的玫瑰不是在子時採下的,我一嘗就知道,露水味不足!」
「你親手製的糟鵪鶉呢?」
「那是要準備留到冬天吃的啊,紅泥小火爐,天雪配鵪鶉,湯包你根本一點意境都不講!」
白樂天的詩不是這樣的!高琮想,但他的舌頭像是被黏在了上顎。常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緩緩地吐了出來。
「我說,任性也要有個限度。天香樓有整整半個月沒有開門了,客人們都在樓下等著呢!這樣下去,怎麼能賺到錢在臨安城開分店?」
「都說過很多次了,沒有想吃的新鮮食物出現啊啊!飲食者,乃是吸納天地,順應四時,與日月共生的大事,一粥一飯都不能敷衍,必須是命中註定,獨一無二的想吃之物啊!在那之前我都不會再次動手的!」
「您老人家盡可以等下去,我還要給我妹妹小梨攢嫁妝呢!」
「小梨小梨!」原本在撒嬌的女聲忽然微妙地轉了調子:「湯包是個大笨蛋!我寧可餓死!」
簾幕後面傳出更多的女子嬉笑聲,聽起來似乎不止一人。
「你不用餓死,至少今天不用。」他朝高琮的方向招了招手。四個露出一臉呆傻表情的苦力將大甕抬了進去,放下後,再一個接一個地走下樓去,竟然連酬勞都忘記跟高琮要。他心底生寒,但眼見大甕已被抬入人家內室,不得不進了門,隱約見有身量嬌小的女子臥在簾幕之後,兩位婢女隨侍在側。他趕緊垂眼束手,站在常青身邊。
「這位是城南望族,高家第二十六代排行第十八位的公子,名琮,字子玉。自幼憊懶厭學,鬥雞賭馬卻無所不能。半年前因為鬧著要娶一名來歷不明的貧家女,被當家的高老太太掃地出門了。」
高琮的冷汗當時就下來了。自己跟阿姣的事情,可算是瞞得隱祕,只有三五個知己知道。無夏城裡絕大多數人見了他,還是得照樣稱呼一聲十八公子。天香樓才開了區區幾個月,怎麼會——
不,不對。他皺起眉來,圓形朱字燈籠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便曾經懸掛在琅琊王府的門外,但天香樓開業的典禮卻千真萬確就發生在三個月前,無夏城裡的芙蓉開得正盛的時候。
但那是今年嗎?那是哪一年?
角落裡,一隻饕餮形狀的薰香爐睜著雙祖母綠的眼珠,緩緩吞吐著紫色的輕煙。他的記憶彷彿被誰活生生撕裂了,再吞噬得一乾二淨。
「不過這甕裡的『新鮮食材』,說不定你會想要試著一吃。」
女子的目光落在一人來高的青花大甕上。從牠被放下的那一刻起,她便起了身,緩緩坐直。那一對婢女得了她的示意從簾中出來,是對雙生子,分別披著桃紅和青蔥色的褙子,朝常青行禮過後,開始慢慢地捲簾。
高琮咽了口唾沫,知道自己即將看到朱成碧——天香樓神祕莫測的女掌櫃的真面目。無夏城中,總共不到二十個人見過她的面,而且每一個人事後都諱莫如深,只說朱姑娘是位絕頂的美人。他緊盯著簾幕一點點升起來的下端,那裡正在緩慢地露出籠著薄紗的茜色襦裙,結著獸形金環的束腰,繪著牡丹的輕羅小扇,還有垂著發帶的雙髻。
雙髻?
高琮瞠目結舌地看著朱成碧站起來,徑直走到大甕面前。他只道她只是身量較小,現在才得以看清,原來發出那麼嬌媚女聲的,不過是一個看起來尚未及笄的小姑娘,頂多有十三、四歲,稚氣未脫的臉還有些殘留的嬰兒肥,一雙大眼漆黑至極,卻有些缺乏神采,彷彿沒有星星的寒冬深夜,只因眼角微微翹起,才稍微帶了點兒嬌俏。
穿青蔥色褙子的婢女捂嘴輕笑,另一個則惱怒地瞪了高琮一眼,他才意識到自己死盯著人家姑娘看,實在是失禮。但朱成碧毫不在意,她的全部主意力都在那隻大甕上面,繞著牠緩慢地踱著步子,轉了整整一圈,接著翹起嘴唇,露出有些發尖的虎牙,心滿意足的笑了起來。
「蟹粉!」她開口喚道:「這個好吃,這個好吃!快取我的鸞刀來!春韭,將我的白梅醋也開一瓶!」
兩位婢女齊齊地望著常青,說不出來的愁苦。他輕嘆一口氣。
「你這亂給人取綽號的脾性什麼時候能改?——去吧,櫻桃,刀架第三層。翠煙,還不照姑娘說的去做?」
*
所謂的鸞刀,是一對兒長不過兩寸的小尖刀,刀柄各自掛了枚金鈴。朱成碧將其執在手中,雙臂略展,凝神屏氣,面上再無一絲嬉笑之色。旁邊翠煙已經擺出了一張烏木小几,放了三隻龍泉窯的碎青小碟,又捧出一隻琉璃罐,將裡面琥珀色的醋挨個兒倒進碟中。那醋味甘甜微酸,縈繞悠長,高琮站在一旁,被這醋味一沖,覺得五臟六腑都像是被洗淨了一般地舒暢,因為薰香而昏沉沉的腦子也忽然清醒過來。
這時候,朱成碧已經朝著大甕一步一步地走了過去,眼看著就要將手放在甕蓋上,他猛然朝前一步,攔住了她。
「姑娘廚藝冠絕天下,這甕中之物本該送給姑娘,但這食材卻也不是平空得來的。」
「要換啥?」
高琮被這直白噎得差點說不下去了,朱成碧只是睜著雙青白無辜的眼睛望著他。
「小生......小生有一事相求——有位貴客,要在八月十五月圓之時路過無夏,懇請朱姑娘出馬,將這千年難遇的珍稀食材,做於他吃。」
她一笑。
「難怪,我說怎會有人平白無故拿這等好吃的來。你所求的,那倒也不是什麼難事。只是你這食材,倒未必是千年難遇。常青,你猜,這裡面裝的是何物?」
一直沉默旁觀的常青吸了吸鼻子。
「海水。含硫磺的砂岩。生鏽的鐵。濃厚的魚腥。這裡最靠近海的,當是錢塘江口的四平鎮,每年的這個季節,漁民都能捕上來胭脂色的海鱸魚,個頭最大的,恐怕也當得起這隻大甕。海鱸堪稱人間珍饌,但要說是千年難遇,卻是言過其實了。」
不對!高琮還沒來得及反駁,只聽朱成碧說:「你這猜測對了一半,卻錯了另一半。胭脂鱸的味道,跟今日這魚腥又有不同,你若仔細分辨,還有另外一種奇異的味道,便像是將珍珠磨成粉,再與海鹽和龍涎細細調和。也難怪,你自幼便在神州大陸,未曾出過海。這種魚,原先在蓬萊周邊的海域最多,蓬萊人誤以為食之能令人長生,爭相捕撈,將沿海的都撈得絕了蹤跡,現在就算有族群,也要往深海裡去找了。能抓到活的,確實難得。」
她走上前,也不知道哪裡來那麼大的力氣,將整個甕蓋朝上一翻,一雙被鐵鍊捆縛,緊貼在蓋子內側的手被一起拉了上來,纖細的手指間生著蹼,還在淋淋漓漓地滴落著海水。
「鮫人鱠!」
朱成碧轉過頭來,歡喜至極地舔著嘴唇,忽然又是那個天真的小姑娘了。 「湯包,我太餓了,現在就做來吃好不好?」
許是聽了她的言語,那鮫人露出頭來,醜陋的臉上顴骨突起,張開了兩側的鰓板,口中只是喝喝作響,卻無人能聽懂牠在說些什麼。
高琮面露懼色,朱成碧卻接著解說:「太平廣記中有言: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下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中。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鱠撥令調勻。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鱠,東南之佳味也。而鮫人鱠的做法,又與鱸魚有所不同,需得在活生生的時候,便自海水中割下——」
她出手迅速,鸞刀上的金鈴只輕響了一聲,水面上升起縷縷血痕。鮫人緊跟著拚命掙扎起來,在甕中猛力甩動著尾巴,咚咚作響。為躲避四濺的海水,高琮後退了一步,內心惶恐不已。朱成碧朝他伸出一隻手,臉上笑吟吟的——
那手上托著巴掌大小的一片肉。通透如冰雪,殊無血跡。
「吃鮫人時,蓬萊人慣用青芥,卻不知青芥辛辣有餘,將鮮味殺得七零八落,最是暴殄天物。鮫人這物在海內長途遷徙,以脊背上的肉質最佳,需得取肋骨之下第七節脊骨上不到三寸大小的一塊,用純金盤盛了,加上頭年的白梅經雪壓凍過的醋漬好,再取香柔花葉,切細了拌勻。可算值得一吃。」
她每說一句,便轉動一次手中的鸞刀,鈴聲停止的時候,看起來還是完整的那塊魚肉忽然一下就在她掌心散開了。她就像是托著一朵盛開的白芙蓉。
朱成碧拈起一片來,直接放入口中,陶醉地說:「不過,直接生吃也別有一番風味。」
高琮的心跳猛地加速了,眼前浮現出阿姣坐在床沿給他縫衣扣的樣子,一隻手戰戰兢兢地抬起來,就要喊出住手兩個字。朱成碧卻忽然臉色一變,呸地一聲將那塊肉吐了出來。
「可惜了可惜了!」她接住常青遞上來的茶,連飲了好幾口,眼睛卻一直盯著地上那塊肉:「如此年輕細滑的鮫肉,偏偏缺少一味重要的滋味,」
高琮腦子裡嗡的一聲。
「怎會......這麼新鮮......您再看看,是活生生切的......」
「新鮮倒是新鮮。」朱成碧轉眼看他:「但她被囚甕中,不得自由,自是愁苦,被人生切,又加驚懼悲痛,如此以來,連血肉都是苦的,哪裡還能有什麼好味道?需得再加一味佐料,好讓她雖身遭千斬萬切,卻無怨無悔,方才能入口。」
「那是什麼?」
朱成碧招手:「你過來,我且說給你聽。」
他遲疑著靠近。此刻,他已經分不清哪些是現實,哪些是虛妄,眼前只有朱成碧將半邊臉都藏在羅扇後面,露出一雙似笑非笑的眼睛,眼角上翹,像是憐憫,又像是嘲諷。
「那一味叫做——愛情。」
尺寸(公分)21*14.8*3.1
開本 25
頁數 608
▌饕餮記【第一部】(上)
第一章 鮫人鱠
第二章 胡眼蜂
第三章 掌間珠
第四章 天地春
第五章 芙蓉焰
第六章 無腸公
▌饕餮記【第一部】(下)
第七章 雙生菇
第八章 同心簽
第九章 千齏麵
第十章 長生餚
番外/天香簿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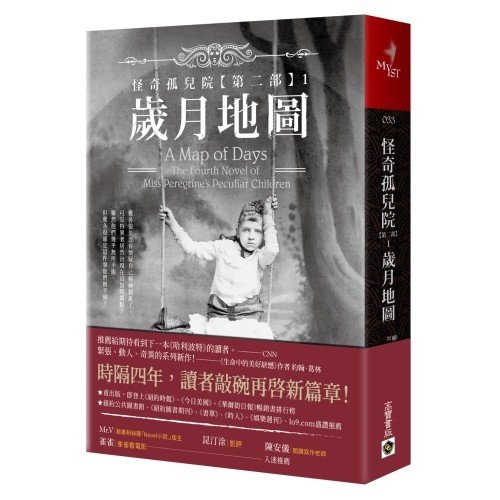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