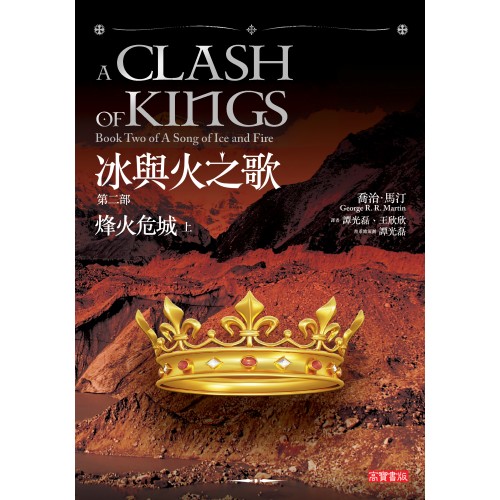會員限定
冰與火之歌外傳:七王國的騎士
NT$284
NT$360
-
作者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
-
譯者趙琳 屈暢
-
ISBN9789863611400
-
上市時間2015-04-15
- 電子書
- BOOKWALKER /
- Readmoo /
- TAAZE /
- 博客來 /
SOLD OUT
-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繁體中文版搶先美國出版
奇幻文學大師喬治‧馬汀全新作品《雇傭騎士》、《誓言騎士》、《神祕騎士》隆重登場
帶讀者回到《冰與火之歌》正傳前八十九年 一窺維斯特洛大陸曾有的風平浪靜 一探九大家族的明爭暗鬥
一揭坦格利王朝的興衰 一述騎士身分的為與不為
失去龍的坦格利安家族,歷經黑火叛亂、血鴉專政,
一場王者的試煉,如何回歸,恢復昔日榮光……
在美國幻想小說大師喬治‧R.R‧馬丁的史詩奇幻經典著作《冰與火之歌》系列小說在台灣引發熱潮,繼續推出了《冰與火之歌外傳:七王國的騎士》,獻給期盼已久的冰火迷。
故事最初是發生在《冰與火之歌》開篇前約八十九年,此時的維斯特洛大陸風平浪靜、一片祥和。「高個騎士」鄧肯懷揣著騎士大夢,和他的侍從、實則身分高貴的小男孩伊戈,一起遊歷世間,尋找圓夢的落腳處……
一路行來,難擋命運的安排,看到黑火叛亂、目睹血鴉專政及貴族與騎士間盤錯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們一步步逼近坦格利安王朝的龍的祕密……消失在人間的龍,卻掌握統治權的龍之血脈,讓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本書首度揭露「冰與火之歌外傳」——《雇傭騎士》《誓言騎士》《神祕騎士》三大故事,其內容不僅揭示了坦格利安王朝的興衰,並暗藏了九大家族的爭鬥,講述不該成王敗寇的真實人生。在跌宕起伏、意外橫生的故事發展中,各種騎士的命運變幻莫測,騎士的精神從而得到徹底展現,
奇幻大師喬治‧馬汀在《冰與火之歌外傳:七王國的騎士》帶給讀者最原生、最草根的維斯特洛,並解謎血火同源的坦格利安家族。
商人們打烊後會把貨車推到草場西陲,一片樺樹和岑樹林裡。鄧克佇立樹下,沮喪地看著原木偶師貨車所在的地方。他們逃了,正如他所擔心的。我要不是比城牆還笨,也該逃的。他不知上哪去找盾牌。身上的銀幣大概夠買一面新的,他估計,假如找得到賣家的話。
「鄧肯爵士。」有人在黑暗中呼喚。鄧克回頭,發現鐵人佩特就站在身後,提著一只鐵燈籠。武器師傅腰部以上只披了件短短的皮革披風,赤裸的寬闊胸膛和粗膀子上覆滿粗糙黑毛。「來取盾的吧?她把盾留下了。」他上下打量鄧克,「俺瞧你手腳無缺,所以明天確實要進行比武審判,是不是?」
「七子審判。你怎麼知道?」
「哈,也許他們會親吻你,封你當領主,可惜這世道,這種事實在不可能;若非如此,就得讓你少受點傷。好了,時間不多,請隨我來。」
鐵匠的車側面繪有劍與鐵砧,老遠都看得見。鄧克隨佩特鑽了進去。武器師傅把燈掛到鉤上,脫掉溼斗篷,當頭套上粗布外衣。他從牆上放下一塊鉸鏈木板權充桌子。「坐。」他說著,隨即推來一張矮凳。
鄧克坐下,「她人呢?」
「他們去冬恩了。是女孩叔叔的決定,很明智。遠走高飛,隱姓埋名。倘若繼續逗留,只怕龍族不會忘記。況且,她叔叔不想讓她看見你死。」佩特在貨車盡頭的陰影中翻找了一會兒,取回盾牌。「你的盾邊緣都是些廉價舊鐵,生了鏽又容易碎。」他指出,「所以我給你打了面新的,比之前的厚兩倍,背後再以鋼筋加固。雖然沉了點,但也結實得多。女孩為你繪了圖。」
她的畫工是他從未見過的。燈籠映照下,落日的色彩異常豐富,茂盛的榆樹挺拔高貴,流星宛如一條掠過橡木天空的明亮彩帶。但鄧克拿在手上,心裡卻不是滋味。墜落的流星,算哪門子徵兆?我會這樣墜落嗎?況且落日意謂著黑夜。「我該留著飛翼杯,」他不無淒涼地說,「至少有翅膀能飛,而阿蘭爵士說那個杯子裡裝滿信仰、希望和一切美好。現在這面盾看似預示著死亡。」
「不,那棵榆樹如此生機盎然,」佩特指出,「看見它的枝葉有多綠嗎?這毫無疑問是夏天的葉子。我這輩子見過無數盾牌,上頭不乏骷髏、惡狼、烏鴉,甚至吊死的人或血淋淋的頭。它們並未預示主人的死亡,這面盾也一樣。你記得那首古老的《盾牌四字歌》嗎?橡木鋼鐵,護衛平安……」
「……保我周全,不墮地獄。」鄧克唱完。他多年沒唱兒歌了,那還是老人很久以前教他的。「這面新盾,你收多少錢?」他問佩特。
「你嗎?」佩特撓撓鬍子,「一個銅板。」
第一縷蒼白晨光滲出東方天際時,雨全停了,但場地也全毀了。亞希佛伯爵命手下移除欄杆,比武場成了一大片灰棕泥巴和爛草的沼澤,地面升起縷縷蜿蜒白霧,宛若條條扭動的白蛇。鐵人佩特陪鄧克上場。
看臺快坐滿了,老爺、夫人們在早晨的清寒中裹緊斗篷,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蜂擁而至。就這麼想看我死啊,鄧克苦澀地想,但他錯怪了他們。他才走幾步,就聽到一個女人扯著嗓子喊:「祝您好運!」一個老人擠出人群來握他的手,「願諸神賜予您力量,爵士先生。」一個穿著破爛褐袍的乞丐幫兄弟吻了他的劍,一位少女衝上來吻他的臉。他們是來支持我的。「為什麼?」他問佩特,「我算什麼?」
「一名謹記誓言的騎士。」鐵匠回答。
雷蒙等在比武場南端盡頭的挑戰者區域外,牽著堂哥的戰馬和鄧克的雷霆。雷霆被沉重的馬頭甲、胸甲和鎖甲毯壓得焦躁不安。佩特仔細檢查這套馬盔甲,雖然不是他的作品,還是大加稱讚。不管是誰貢獻出這套馬盔甲,鄧克感激不盡。
然後看見了加入他這方的人:花白鬍子的獨眼騎士,盾牌和罩袍繪有黑黃條紋上三個蜂窩的年輕騎士。羅賓.羅辛林爵士和韓佛雷.畢斯柏里爵士。他震驚地意識到。韓佛雷.哈汀爵士也來了。他騎在伊利昂的紅色戰馬上,只是那馬已覆上紅白相間的菱形紋章。
他走向三位騎士,「爵士們,我永遠欠你們的情。」
「是伊利昂欠我們,」韓佛雷.哈汀爵士回答,「我們要找他討回。」
「聽說您腿折了。」
「不錯,」哈汀承認,「我下不了地。但只要能騎馬,我就能戰。」
雷蒙將鄧克拉到一旁,「我盤算哈汀渴望再次面對伊利昂,果真不出所料。更幸運的是,另一位韓佛雷原來是他連襟。羅賓爵士是伊戈找的,他們在別的比武會上有交情。現在我方有了五人。」
「六人,」鄧克難以置信地伸出手指,只見一名雄赳赳的騎士踏步而來,侍從牽著他的戰馬,「狂笑風暴!」萊昂諾爵士比雷蒙爵士高出一個頭,幾乎與鄧克一樣高,金線罩袍上繡著拜拉席恩家的寶冠雄鹿,鹿角盔夾在腋下。鄧克伸出手,「萊昂諾爵士,真不知要如何感謝您和邀請您的史蒂芬爵士。」
「史蒂芬爵士?」萊昂諾爵士奇道,「是你的侍從來找我。那男孩伊耿。我家小子想趕他走,他一個箭步就從我家小子的雙腿間鑽了過去,朝我頭上潑了一壺酒。」他哈哈大笑。「要知道,一百多年沒舉行七子審判了!我可不願錯過與御林鐵衛較量、順便挫挫梅卡王子威風的機會。」
「現在有六個人,」萊昂諾爵士去招呼其他騎士時,鄧克滿懷希望地對雷蒙.佛索威說,「我敢肯定,你堂哥至少能請來一個人。」
人群中爆發出一陣吶喊。草場北端,一隊騎士自河岸的晨霧中奔出。當先是三位瓷釉白甲的御林鐵衛,猶如三道幽靈,長長的白袍在身後翻飛,連盾上也乾乾淨淨、空無一物,宛若新雪。鐵衛之後是梅卡王子及其兩個兒子,伊利昂騎著匹灰斑駿馬,馬飾上的橙、紅流蘇一路耀武揚威;他弟弟戴倫的戰馬則小一號,通體裹著黑金鱗甲,頭盔上飄揚著綠絲羽毛。然而,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是他們的父親,梅卡雙肩裝飾著彎曲的黑色龍牙,頭盔和背上也有,馬鞍掛了一把碩大的釘頭錘,那是鄧克見過最恐怖的武器。
「六個,」雷蒙忽然叫道,「他們也只有六個人。」
是的,鄧克發現了,對方有三名黑騎士、三名白騎士,但還缺了一個人。難道伊利昂找不到人助拳?這意謂著什麼?審判將以六對六,而非以七敵七?
他正冥思苦想,伊戈悄然來到身旁,「爵士,該穿盔甲了。」
「謝謝你,侍從。幫個忙?」鐵人佩特和男孩合力為他穿上鎖甲、護喉、護脛、護手、頭盔與股囊。一樣接一樣,他們把他武裝到牙齒,又反覆檢查每個帶釦、搭釦。萊昂諾爵士在旁用油石磨劍,兩個韓佛雷低聲交談,羅賓爵士在祈禱,而雷蒙.佛索威則焦急地來回踱步,擔心堂哥的去向。
待鄧克披掛整齊,史蒂芬爵士才姍姍來到。「雷蒙,」他使喚堂弟,「快,把我的鎖甲拿來。」他已穿好鎖甲裡的加墊上衣。
「史蒂芬爵士,」鄧克道,「你請到朋友了嗎?我們還需要一位騎士才能湊足七人。」
「恐怕你還需要兩位,」史蒂芬爵士回答。雷蒙替他繫好鎖甲。
「大人,」鄧克不明白,「兩位?」
史蒂芬將一只精良的鐵製龍蝦護手套進左臂,然後活動手指。「我只看見五人,」雷蒙替他綁上劍帶。「畢斯柏里、羅辛林、哈汀、拜拉席恩和你自己。」
「還有你啊,」鄧克說,「加上你就是六個。」
「我是第七人,」史蒂芬笑道,「不過是另一邊的。我已加入伊利昂王子一方。」
雷蒙正打算給堂哥戴上頭盔,聽罷此言如五雷轟頂,「不。」
「是的,」史蒂芬爵士聳肩,「相信鄧肯爵士會理解,我有義務效忠王子殿下。」
「你說找騎士的事包在你身上。」雷蒙面如土色。
「我說過?」他從堂弟手中抓過頭盔,「我那時無疑是真心的。把坐騎給我牽來。」
「你自己去牽。」雷蒙忿然道,「如果你以為我還會幫你,那你不僅爛到了芯兒裡,臉皮比城牆還厚。」
「爛到了芯兒裡?」史蒂芬爵士咂嘴。「管住舌頭,雷蒙。我們是一棵樹上的蘋果,而你是我的侍從。你忘記誓言了嗎?」
「我從未忘記。但你呢?你發誓當一名好騎士。」
「明天我就不止是騎士啦。佛索威伯爵聽來如何?我挺喜歡。」他微笑著套上另一只護手,轉身去牽馬,無視於周遭鄙視的目光。沒人出手阻止。
鄧克眼睜睜看著史蒂芬爵士牽馬穿過場子,怒不可遏地握手成拳,但乾澀的嗓子說不出一句話。說什麼也無法挽回佛索威。
「請賜封我為騎士,」雷蒙一隻手放在鄧克肩上,用力扳他過來,「讓我頂替堂哥。鄧肯爵士,請賜封我為騎士。」他單膝跪下。
鄧克躊躇地握住劍柄,皺起眉頭。「雷蒙,我……我不知道。」
「你必須這麼做,不然你只有五個騎士。」
「這孩子說得對。」萊昂諾.拜拉席恩爵士插話,「事不宜遲,鄧肯爵士,任何騎士都能賜封騎士。」
「你質疑我的勇氣嗎?」雷蒙問。
「當然不,」鄧克說,「當然不,我只是不想……」他還在猶豫。
一陣喇叭聲穿透晨霧,伊戈急急忙忙跑來。「爵士,亞希佛大人召喚你。」
狂笑風暴不耐煩地搖頭,「你快去,鄧肯爵士,我來賜封侍從雷蒙。」他飛快抽出長劍,用肩擠開鄧克。「佛索威家族的雷蒙,」萊昂諾爵士莊重地將劍放在侍從的右肩,「以戰士之名,我要求你勇敢。」長劍從右肩移至左肩。「以天父之名,我要求你公正。」回到右肩。「以聖母之名,我要求你保護弱者和無辜之人。」左肩。「以少女之名,我要求你保護所有婦女。」
鄧克留下他們繼續儀式,感覺心中放下一塊石頭,卻又充滿罪惡感。還差一人,他翻身跳上伊戈為他牽住的雷霆,我上哪再找一個人?他調轉馬頭,緩緩騎向亞希佛伯爵等候的看臺。伊利昂王子從比武場北端騎來會他。「鄧肯爵士,」他興高采烈地說,「你方好像才五人啊。」
「六人,」鄧克反駁,「萊昂諾爵士正在賜封雷蒙.佛索威。我們將以六敵七。」哪怕眾寡更懸殊,卻也不是毫無機會,但亞希佛伯爵搖頭,「不行,爵士,若你找不到另一名騎士,即證明你所受指控為實,將被判有罪。」
有罪,鄧克心想,打掉一顆牙齒的罪,為此我將賠上一條命。「大人,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可以。」
鄧克緩緩地在看臺前騎行,臺上擠滿騎士。「大人們,」他大聲疾呼,「你們肯定還有人記得銅分樹村的阿蘭爵士。我是他的侍從,我們曾為您效勞,曾在您桌旁用餐、在您廳堂休息。」他發現曼佛德.唐德利恩坐在最高一排。「阿蘭爵士為您父親大人效勞時受過傷。」那騎士只顧著與身邊貴婦說話,壓根不理他。鄧克只能轉向其他人。「蘭尼斯特大人,阿蘭爵士曾在比武會中將您打下馬。」灰獅檢查著手套,打定主意不抬眼。「他是個好人,他教會我騎士之道,不僅是使槍弄劍,更在於榮譽。要保護無辜之人,他這麼教誨,我如此遵行。現在,我需要一位騎士與我並肩作戰。我只要一位騎士。卡隆大人?史文大人?」卡隆伯爵湊在史文伯爵耳邊說了什麼,史文伯爵輕笑出聲。
鄧克在奧索.布雷肯爵士面前勒馬,壓低聲音:「奧索爵士,眾人皆知您是一位偉大的騎士。請您加入我們吧!我懇求您,以新舊諸神之名,我的訴求是正義的。」
「也許吧,」屠夫布雷肯好歹肯當面回答,「但這不關我的事。我不認識你,小子。」
鄧克心如刀絞,他調轉雷霆,在一排排漠然的冷血動物面前騎來騎去。絕望中,他忿然大吼:「你們中就沒有一位真正的騎士嗎?」
一片靜默。
伊利昂在場子對面哈哈大笑。「真龍絕不會失敗。」他大叫。
這時有人回應:「我來加入鄧肯爵士。」
晨霧中河岸邊緩緩騎出一匹黑色駿馬,馬上有位黑騎士。鄧克看見龍盾和頭盔上三個咆哮的琺瑯龍頭。少王子。諸神在上,真的是他?
亞希佛伯爵同樣錯認。「瓦拉爾王子?」
「不。」黑騎士掀開面甲。「我沒打算來白楊灘參賽,大人,所以沒帶盔甲。虧得我兒好心出借。」貝勒王子的笑容幾乎有些哀傷。
鄧克發現,控方騎士陷入了混亂。梅卡王子催馬上前。「哥哥,你失去理智了嗎?」他用一隻套著鐵甲的指頭指向鄧克。「這個人襲擊我的兒子。」
「此人保護弱者,正如每位真正的騎士該做的那樣。」貝勒王子回答,「讓天上諸神決定他是否有罪吧。」他一拉韁繩,調轉瓦拉爾的大黑馬,奔向比武場南端。
鄧克騎雷霆跟上,為他而戰的其他騎士也圍攏過來:羅賓.羅辛林和萊昂諾爵士,兩位韓佛雷。他們都是好人,但也都是好手嗎?「雷蒙呢?」
「拜託,是雷蒙爵士,」他小跑上來,微笑點亮了羽盔下嚴肅的臉。「請原諒,爵士,我剛才對紋章做了點小改動,我可不想再跟我那不名譽的堂哥同流合污。」他把新塗裝的盾牌拿給他們看――閃亮的金底依舊,但佛索威的紅蘋果成了綠蘋果。「恐怕我真的沒熟……但青蘋果總比爛蘋果好,呃?」
萊昂諾爵士哈哈大笑,鄧克也忍不住咧嘴笑,連貝勒王子都表示讚許。
亞希佛伯爵的修士來到看臺前,舉起水晶,帶領大家祈禱。
「現在,各位請靠近,」貝勒靜靜地說。「控方衝鋒時會使沉重的戰槍,八尺長的岑樹槍,鐵條加固以防斷裂,鋒利的鐵尖加上坐騎的衝力,足以戳穿全身甲。」
「我們也該同樣應對。」韓佛雷.畢斯柏里爵士道。修士在他身後呼喚天上七神作證,做出公正裁決,將勝利賜予正義一方。
「不,」貝勒反對,「我們用比武長槍。」
「比武長槍容易斷。」雷蒙指出。
「但它們有十二尺長,只要瞄得準,他們的槍根本碰不到我們。瞄準頭或胸,比武時在對手盾上撞斷長槍很英勇,實戰中就可能是送死。打對手下馬自己坐得住,勝利十拿九穩。」他瞥了鄧克一眼。「若鄧肯爵士有個閃失,比武審判將以諸神判他有罪結束;若他的兩位指控者被殺,或至少撤回指控,結局與之相反。若以上兩項都不能得到滿足,則必須打到某方七人全部喪命或投降。」
「戴倫王子不會打。」鄧克說。
「反正他也打不好,」萊昂諾爵士大笑,「我們的不利在於要對付三名白騎士。」
貝勒平靜以對,「我弟弟不該命御林鐵衛為他兒子出戰。然而他們的誓言禁止他們傷害流著真龍血脈的王子,幸運的是,我也是個王子。」他朝大家淡淡一笑,「你們替我擋住其他人,我來對付御林鐵衛。」
「殿下,這樣是否有失騎士的體面?」修士完成禱告,萊昂諾.拜拉席恩爵士疑惑地問。
「只有諸神知道。」破矛者貝勒說。
深沉的靜默,一如預期籠罩了白楊灘草場。
八十碼外,伊利昂的灰戰馬煩躁地嘶鳴,扒拉泥濘地面;雷霆卻格外安靜,牠畢竟是匹身經百戰的老馬,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麼。伊戈把盾遞給鄧克。「願諸神與您同在。」男孩說。
盾上的榆樹和流星振作了他。他左手穿進繫帶,握緊握把。橡木鋼鐵,護衛平安,保我周全,不墮地獄。鐵人佩特送上長槍,但伊戈執意要親自呈給鄧克。
左右兩邊,他的戰友也紛紛拿起長槍,排成戰列。貝勒王子在右,萊昂諾爵士在左,但巨盔的狹長眼縫讓他只能關注正前方。看臺不見了,籬笆後的群眾也不見了,眼前唯有泥濘的場地,絲絲縷縷的白霧,北方的河流、市鎮和城堡,以及那個騎在灰馬上、盔頂有龍焰裝飾、盾牌上有隻趾高氣揚的龍的王子。鄧克目睹伊利昂的侍從送上漆黑如夜的八尺戰槍。他大概想刺穿我的心臟。
一支號角吹響。
剎那間,鄧克彷如封在琥珀中的蒼蠅般僵坐不動,但所有的馬同時奔跑起來。突如其來的恐懼刺穿了他。我傻了,他狂亂地想,我完全傻了,我會一敗塗地、辜負大家。
雷霆拯救了他,棕色大戰馬什麼都記得,無須騎手催促,便開始小跑。鄧克下意識地用上訓練的成果,馬刺朝戰馬輕輕一扎,放低長槍,舉盾護住左邊大半身體。他握盾的角度是要擋開可能的刺擊。橡木鋼鐵,護衛平安,保我周全,不墮地獄。
人群的喧譁減弱為遙遠的浪濤,雷霆邁步飛奔,鄧克在疾速奔馳中咬緊牙關。他放低馬刺,用盡全力夾緊大腿,讓人馬合一。我是雷霆,雷霆是我,我們是同一頭野獸,我們融在一起,我們是一體。頭盔裡變得如此悶熱,他幾乎無法呼吸。
長槍比武中,對手會從左邊攻來,隔著一道欄杆,而他的長槍會橫過雷霆的脖子。那種角度下槍很容易折斷。但今日乃是死鬥,戰馬正面對衝,之間全無阻礙。貝勒王子的大黑馬比雷霆快得多,鄧克從眼縫邊瞥見王子衝在前頭。他沒再探視其他人,他們都不重要,只有伊利昂,伊利昂才是他的焦點。
他看見騰飛的巨龍。伊利昂王子的灰馬鼻孔大張,蹄下濺起無數泥點。黑色戰槍依然高舉。騎士若到最後一刻才放槍,有瞄低的危險,老人指導過他。他的槍尖對準了王子的胸膛。槍和手是一體,他告訴自己,它是手的延長,是我的木手指。我只需用長長的木手指碰他一下。
他試圖忽略伊利昂黑槍上迅速擴大的銳利尖頭。龍,看那條龍,他心想。巨大的三頭怪獸覆蓋了王子的盾牌,紅色翅膀,金色火焰。不,看你要刺的地方,他猛然驚覺,但長槍已偏了方向。鄧克奮力糾正,可為時已晚,槍尖砸在伊利昂盾上兩個龍頭之間,刺進一團彩繪火焰。隨著一聲悶響,雷霆受到阻力,在撞擊的力道下顫抖,半個心跳後,有東西憑著一股怪力擊中他身側,接著兩馬劇烈相撞,盔甲叮鈴噹啷,雷霆跌跌撞撞。鄧克長槍脫手,越過了對手,死命抓住馬鞍才沒跌倒。雷霆在爛泥地裡東倒西歪,鄧克覺得馬的後腿失去了控制,人和馬不住打滑、轉圈,然後雷霆一屁股坐倒。「起來!」鄧克大吼,猛踢馬刺,「起來,雷霆!」老戰馬在他的命令聲中不知為何又站了起來。
肋下劇痛,左臂不聽使喚。伊利昂的長槍穿透了橡木、羊毛和鋼鐵,三尺長的斷裂岑木和鐵尖插在他身上。鄧克伸出右手握住斷槍底部,咬緊牙關,死命用力將之扯出。鮮血泉湧,滲過鎖甲鏈環,浸透罩袍。他只覺天旋地轉,直欲落馬,然而矇矓中,隔著雨簾隱隱聽到人們在呼喚他的名字。他美麗的盾牌失去了效用,他把它們統統扔開,榆樹、流星、斷槍統統扔掉後,他抽出長劍。但他傷得太厲害,大概沒力氣使它。
他驅策雷霆轉圈,試圖弄清楚周圍戰況。韓佛雷.哈汀爵士伏在馬脖子上,顯然受了傷。另一位韓佛雷爵士人事不省地倒在一灘鮮血染紅的泥巴裡,股間插了一截斷槍。貝勒王子仍在奔馳,長槍也完好無損,他把一位御林鐵衛挑下馬。梅卡和另一位白騎士已然落馬。第三位御林鐵衛正在和羅賓.羅辛林爵士纏鬥。
伊利昂,伊利昂呢?身後的隆隆馬蹄讓鄧克猛然回頭。雷霆嘶叫人立、四腳亂踢,伊利昂的灰戰馬全速撞上了他。
這回他再也無法恢復平衡。長劍旋轉脫手,地面迎頭撞來,他結結實實摔了一跤,摔得骨頭打顫、痛徹心肺、眼淚橫流。他沒力氣了,嘴裡滿是血味。呆子鄧克,自以為是騎士。他必須起來,否則難逃一死。於是他手腳並用呻吟著起身,無法呼吸,目不視物,頭盔眼縫沾滿泥巴。他只能盲目地爬起來,用鐵甲手指刮除眼縫中的泥巴。是了,那是……
透過指縫,他看見飛翔的巨龍和鐵鍊盡頭的帶刺流星錘。然後腦瓜炸成碎片。
等他再度睜眼,發現又躺在地上,摔得四腳朝天。頭盔上的泥巴統統被震落,但一隻眼睛為血蒙住,另一隻眼睛只見黑灰天空。面龐陣陣抽痛,冰冷溼潤的鐵貼緊臉頰和額頭。他砸破了我的頭,我快死了,還連累大家,雷蒙、貝勒王子和所有人。我終於還是辜負了他們。我不是冠軍,甚至沒資格當雇傭騎士。我一無是處。他想起戴倫王子吹噓自己躺泥巴裡裝死的本領是冠軍。他不知鄧克更能裝,對吧?這份恥辱比疼痛更讓他難受。
巨龍籠罩在他面前。
龍有三個頭,翅膀亮如火焰,紅、黃和橙。龍獰笑著。「死了沒有,雇傭騎士?」龍問,「求饒認罪,本王或許只要你一手一腳。噢,外加所有牙齒。牙有何用?反正你這等賤貨只配喝粥。」龍仰天長笑。「不投降?嘗嘗這個。」帶刺鐵球在空中旋轉,勢如流星砸向他的頭。
鄧克突然翻身。
他不知哪來的力氣,一下滾到伊利昂腳邊,用鐵甲包裹的胳膊抱住對方大腿,將咒罵著的王子拖進泥地,隨即翻到上面。他儘管用那該死的流星錘砸吧!王子試圖拿盾敲鄧克的頭,但被砸扁的頭盔承受了衝擊。伊利昂固然強壯,鄧克卻更壯、更大、更沉。他雙手抓盾,竭力扳動,直到繫帶斷裂,然後拿它往下砸王子的頭盔,一下一下又一下,砸碎了頭盔上的琺瑯火焰。這面鐵皮鑲邊的堅實橡木盾比鄧克的盾更厚。一條火焰碎裂,接著又一條,鄧克沒幾下就砸掉了王子所有的火焰。
伊利昂終於鬆開無用的流星錘,摸向臀間匕首。他剛把它拔出鞘,鄧克就用盾砸去,匕首脫手飛進泥土中。
王子打敗了高個鄧肯爵士,卻在跳蚤窩的鄧克面前敗下陣來。老人將槍劍技巧傾囊相授,但打架是他從小熟悉的,從小在都城貧民窟的暗巷角落間練就的。鄧克扔掉破盾,扯開伊利昂的面甲。
面甲是弱點,他還記得鐵人佩特的話。王子停止了掙扎,青腫眼睛裡寫滿恐懼。鄧克突然有股衝動,想用兩根鐵甲手指像摘葡萄般捏下王子的眼球,可惜這有違騎士精神。「快投降!」他大吼。
「我投降,」龍低聲說,蒼白的嘴唇幾乎沒動。鄧克俯身眨眼打量他,一時間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切都結束了,是嗎?他緩緩轉頭,想看清此時戰況。頭盔左側挨的那記重擊,封閉了部分眼縫,他只見梅卡王子揮舞釘頭錘衝向兒子,卻被破矛者貝勒擋住。
鄧克拖著伊利昂王子,搖搖晃晃起身。他胡亂摸索頭盔,然後將其扯掉扔開,瞬間被聲音和視覺淹沒:悶哼、詛咒、人群叫喊、一匹戰馬的淒鳴、另一匹沒了騎手的戰馬飛馳而過。到處是刀光劍影。雷蒙和他堂哥在看臺前徒步廝殺,兩面盾牌均被打碎,綠蘋果和紅蘋果都已糜爛。一名御林鐵衛的騎士扶著受傷的兄弟退出比武,兩人白甲白袍,分不清誰是誰。另一名白騎士業已倒下,狂笑風暴得以協助貝勒王子對抗梅卡王子,一時間釘頭錘、戰斧和長劍你來我往,鏗鏘地砸在盔和盾上。梅卡每反擊一次,就要承受三倍的攻擊,看來敗局已定。我必須做點什麼,阻止無謂死傷。
伊利昂突然撲向流星錘。鄧克朝他後背踢了一腳,踩他個狗吃屎,然後拉起他的一條腿,拖過場子。來到看臺上的亞希佛伯爵面前,明焰王子渾身已是屎一般的顏色。鄧克用力拉他起來,使勁搖晃,也不管濺了老爺和美少女一臉土。「說!」
明焰伊利昂吐出一口青草泥巴,「我撤回指控。」
之後鄧克記不清是靠自己還是憑藉別人幫助才走出場外。他遍體鱗傷,有的部位痛得很厲害。我是貨真價實的騎士了嗎?他記得自己想過,我是冠軍了嗎?
伊戈、雷蒙和鐵人佩特幫他除去護脛、護喉,他迷迷糊糊分不清他們,只覺眼前一片手指、拇指,還有聲音。抱怨的是佩特,鄧克心想。「瞧瞧,我的盔甲成什麼樣了,」鐵匠發牢騷,「到處是擦刮不說,還凹進去變了形。哈,你們要問,這還關我啥事?算了,我得把鎖甲割下來。」
「雷蒙。」鄧克急切地抓住朋友的雙手,「其他人呢,他們好嗎?」他必須知道,「有人死嗎?」
「畢斯柏里遭遇不幸,」雷蒙回答,「他第一輪衝鋒就倒在暮谷城的唐納爾槍下,韓佛雷爵士也傷得很重。其他人只是皮外傷,流了些血,不礙事。除了你。」
「他們呢?控方呢?」
「御林鐵衛威廉.威爾德爵士昏迷不醒,被抬出場治療。我打斷了堂哥幾根肋骨,至少我如此希望。」
「戴倫王子呢?」鄧克脫口而出,「他還活著吧?」
「羅賓爵士挑他下馬,他就一動不動了。可能斷了腿,他的坐騎亂竄踩到他一次。」
鄧克雖然眩暈又迷茫,卻感到一股巨大的欣慰。「他的夢沒成真。沒有龍死去。除非伊利昂死了。伊利昂沒死,對吧?」
「沒有,」伊戈道,「您饒了他。您不記得了嗎?」
「大概吧。」戰鬥場景已變得混亂模糊,「我像是醉了,但好痛好痛,只怕離死不遠。」
他們扶他躺好,一直陪他說話,而他呆看著烏雲翻捲的天空。好像還是清晨,不知比武究竟持續了多久。
「諸神在上,鏈環被槍尖頂了進去。」他聽見雷蒙說,「會感染,除非……」
「把他灌醉,朝傷口倒沸油。」有人建議,「我見學士這麼幹。」
「沸酒。」一個金屬般空洞的聲音插進來,「不是沸油,那會害死他。用沸酒。等約爾威學士照料好我弟弟,我就叫他過來。」
一名高大騎士籠罩在前,身上黑甲傷痕累累、坑窪處處。貝勒王子。王子盔上的紅龍失去了龍頭、雙翼和大半個尾巴。「殿下,」鄧克說,「從今往後,我要為您效勞,就算粉身碎骨也難報您的大恩大德,我要為您效勞。」
「為我效勞,」黑騎士一手扶在雷蒙爵士肩上,穩住自己,「我的確需要好人,鄧肯爵士,王國……」他的聲音古怪,以致聽不太清楚,似是在打鬥中咬到舌頭。
鄧克身心俱疲,保持清醒已屬不易。「為您效勞。」他呢喃著再重複一遍。
王子緩緩搖頭。「雷蒙爵士……我的頭盔,幫個忙,面甲……面甲碎了,而我的指頭……麻木……」
「讓我來,殿下,」雷蒙雙手抓住王子的頭盔,哼了聲,「好佩特,幫個忙。」
鐵人佩特拖來一張板凳。「後面給砸扁了,殿下,左邊砸進護喉裡。這頭盔真不賴,能承受如此重擊。」
「多半是拜我弟弟的釘頭錘所賜,」貝勒甕聲甕氣地說,「他很強壯,」他身子一縮。「呃……有點怪,我……」
「取下來了,」佩特扔開破頭盔,「諸神在上,噢諸神啊噢諸神啊噢諸神啊諸神啊……」
鄧克發現有個紅紅溼溼的東西隨頭盔落地,接著有人驚恐萬狀地發出尖銳叫聲。淒冷灰暗的天幕之下,高大的黑甲王子只剩半顆頭顱,他看到殷紅的血和森森白骨,以及果肉般的藍灰事物。破矛者貝勒露出奇特的苦笑,宛若那將要被烏龍遮掩的太陽。他抬起一隻手,用兩根指頭摸摸腦後,噢,無比輕柔。
然後他砰然倒下。
鄧克一把接住他。「起來!」他們說他像比武時命令雷霆一樣大吼,「起來!起來!」後來的事他全不記得,只知王子終究沒再起來。
坦格利安家族的貝勒,龍石島親王,御前首相,全境守護者,君臨維斯特洛七大王國的鐵王座的繼承人,在舟徙河北岸白楊灘堡的庭院裡被火葬了。其他各大家族或將死者埋在黑暗地底、或沉入冰冷汪洋,但坦格利安家是真龍血脈,火是他們的歸宿。
他是當今最優秀的騎士,很多人認為他離世時應該全身披掛、手握長劍,但最終他君父的願望占了上風,戴倫二世天性平和。鄧克拖著腳走過貝勒的棺木,只見王子殿下穿著胸前以猩紅絲線繡了三頭龍的黑天鵝絨外套,喉頭掛著沉重金鏈,入鞘寶劍置於身旁。他戴著頭盔,只是一頂薄薄的鍍金盔,沒有面甲,好讓眾人能瞻仰遺容。
少王子瓦拉爾在棺木尾端守靈,迎接弔唁者。他是乃父更矮小、更瘦弱、更俊美的翻版,且沒有那斷掉兩次、讓貝勒看似平民不似王族的鼻子。瓦拉爾是棕髮,但間雜了一束耀眼的銀白,這讓鄧克想起伊利昂。他知道這不公平,畢竟伊戈的頭髮也長回來了,和兄長的一樣閃亮,但伊戈毫無疑問是個好孩子。
他停步說出尷尬的禱語,試圖表達無盡的謝意,瓦拉爾王子眨著冰冷的藍眼睛。「家父才三十九歲,他本該帶給七大王國一個流芳千載的太平盛世,本該成為自龍王伊耿以降最偉大的國王。憑什麼諸神帶走他、留下你?」他不住搖頭,「離開,鄧肯爵士,我不想看見你。」
鄧克無言地跛行離開城堡,回到綠池塘旁的營地。對於瓦拉爾的質問,他沒有答案,他的困惑太多太多。大夫和沸酒治好了他,傷口已無大礙,但左手和左邊乳頭卻從此落下深深的褶皺傷疤。每當看到傷疤,他就會想起貝勒。他用劍救了我一命,說出的建議又救了我一次,雖然他來到我身邊時其實已是個死人。世道真是奇怪,偉大的王子死去,卻讓卑微的雇傭騎士活著。鄧克坐在榆樹下,憂鬱地盯著腳。
15*21公分
前情提要
雇傭騎士
誓言騎士
神祕騎士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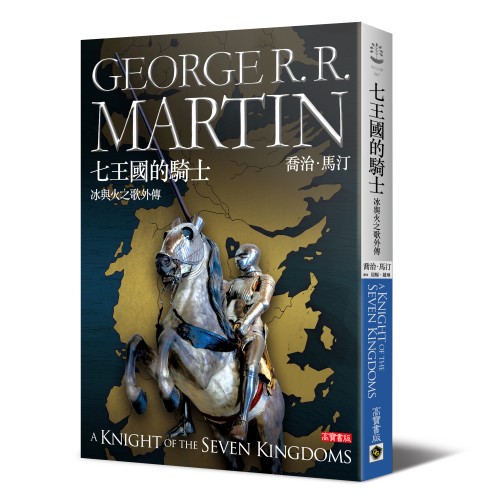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