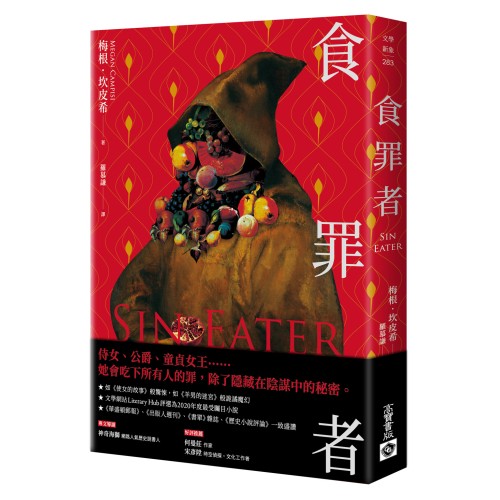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千門(一):千門之門》+《千門(二):千門之花》
古裝大戲《雲襄傳》原著小說!
★2022年網友最期待影劇,愛奇藝磅礡出品
★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陳曉、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女配角提名 毛曉彤、唐曉天 領銜主演!
★千年武俠史上,前所未見的智俠傳奇!
首開連載以來即備受矚目,作者方白羽新修版本,時隔14年全新上市!
「人,既無虎狼之爪牙,亦無獅象之力量,卻能擒狼縛虎,馴獅獵象,無他,惟智慧耳。」――《千門祕典》
◆《千門(一):千門之門》
相傳大禹創立千門一派,得千門者即能謀天下,
然千門之人行事詭祕,善於藏身幕後操弄風雲,
因而在歷史長河中,千門一派逐漸成為鮮有人知的傳說,
直到大明末期,《千門祕典》重出江湖,天下將會掀起何等的波瀾。
─
曾經的理想與堅持都已死在那如地獄般的牢籠裡,
從此刻起,他將以雲襄之名重生,而他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復仇。
母親暴斃猝死,未婚妻子改嫁仇人,族中老幼流離失所,駱文佳披枷帶鎖走在流放到荒漠邊境的路上,腦中不斷浮現那個奪走他所有人生希望的南宮放。他在心中立誓,定要逃離這沙漠牢獄,手刃他的仇人,拿回屬於他的一切。然而,他不過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窮書生,就算能逃出生天,孑然一身的他又要如何對抗家大勢大、足以隻手遮天的南宮世家?
當一切希望都不復存在,就連他的性命也即將告終的時候,天下人尋而不得的江湖傳說竟活生生出現在他眼前……
◆《千門(二):千門之花》
賭博是一門在方寸間勾心鬥角的學問,
在常人眼裡,它賭的是技術和運氣,
但在千門中人眼裡,鬥的卻是智謀。
─
她是與他旗鼓相當的千術高手,
她是與他命運相同的亡命之徒,
她是帶著雨花石,將他的「心」握在掌中的命定之人。
雲襄帶著金彪再次踏上揚州的土地,為了在揚州站穩腳跟、壯大實力與南宮家抗衡,他隱瞞身分投入莫爺麾下。本以為自己得雲爺真傳,千人應無敵手,豈料卻意外栽在舒亞男手上,成為對方調侃的「跑腿小騙子」。這個舒亞男究竟是何來歷,連南宮家長子都被她千得血本無歸,雲襄除了復仇別無他想的心,也不禁泛起漣漪。
達摩聖寂日即將來臨,雲襄奉莫爺之命前往盜取少林鎮寺之寶,舒亞男也受人委託爭奪同一目標,兩人再次交手,各不相讓,然而真正的千門之王尚未露出他的真實面目……
【讀者燒腦好評】
◆ 另闢蹊徑的武俠故事,鬥智鬥勇,手無縛雞之力卻能縱橫天下,唯千門也。
◆ 這種風格偏向一點懸疑、以鬥智為主的武俠小說,更能讓讀者感到過癮。
◆ 《千門》無論從閱讀快感,還是從啟發性而言,都是一部精采的小說。
◆ 從千門開始,才真正體會到武俠的魅力!
►《千門》全六冊 即將出版
《千門(三):千門之雄》
《千門(四):千門之威》
《千門(五):千門之心》
《千門(六):千門之聖》
楔子
天高地闊,萬里無雲,赤紅的太陽紋絲不動地高懸中天,把天地映照得亮晃晃一片紅火。空氣被日光燒灼得熾熱難當,似乎只差一點火星就能點燃。在如此酷烈的天氣下,一望無際的戈壁大漠中,有一小隊奇怪的人馬掙扎著在無路可循的黃沙裡前行,人數不足二十,騾馬牲口不及十頭。除了領頭的四五人騎有騾馬駱駝,其餘十多人竟被鐐銬栓在一起,像騾馬一般繫成一串,在幾個騎者的吆喝鞭笞下,勉強向前蠕行。
在如此酷烈的陽光下,戈壁荒漠本就不多的活物也都躲到各自的藏身之處,以避開一天中最毒辣的光線。放眼望去,前方那漫漫黃塵天地裡,除了東一團、西一簇的駱駝刺,就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驛站。驛站旗竿上那方懶洋洋隨風擺拂的破旗,勉強透出一絲難得的生氣。看到那面旗幟,幾個騎手不禁一聲歡呼,鞭笞眾囚徒加快了步伐。
驛丞老蔫也看到了這一小隊人馬,遠遠便步出驛站相迎。老蔫並不是個熱情好客的主兒,整天都蔫巴巴像霜打茄子 ,不過,任誰在這遠離人煙的荒僻驛站孤零零呆上十年,見到強盜都會覺得親切。
「老蔫!快快準備清水草料!這鬼天氣,簡直要把人給烤熟了!」領頭的騎者遠遠就在大叫,他的臉上有一道血紅的刀疤,隨著表情變化不住蠕動,遠遠看去,就像臉頰上又開了一張口。
「清水草料早已經準備好!刀爺!」老蔫邊答應著,邊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清水和草料。他認得來人是甘涼道有名的捕頭,綽號刀疤,真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這裡雖然已是青海地界,但刀疤經常負責把內地送到甘涼道的囚犯,再押送到更遠的青海服苦役,因而時不時要經過這座孤零零的驛站,一來二去,與老蔫自然就相熟起來。
幾個衙役翻身下馬,爭先恐後地奔向老蔫準備好的清水饅頭,幾個披枷帶鎖的囚犯則跌跌撞撞地躲到陰涼處,東倒西歪地癱在地上直喘粗氣,就像幾條離了水的魚。
老蔫提了一桶清水向他們走去,他雖然知道發配到如此荒涼偏遠之地來服苦役的囚犯,大都是些窮凶極惡之輩,不值得同情,但一個人在這驛站苦守多年,一年到頭難得看到幾個人,就算是囚犯,在老蔫眼裡也十分親切。
老蔫舀了一瓢水,幾個囚犯立刻爭先恐後伸長脖子張嘴來接。囚犯都戴著枷,雙手不得自由,吃喝拉撒都得要人幫忙。老蔫正要餵,卻聽身後一個衙役喊道:「等等!」
老蔫莫名其妙地回過頭,就見一個吃飽喝足的差役,抹著嘴一臉壞笑地過來,奪過老蔫手中的水瓢扔回桶中,然後兩腿一叉,扯開褲子對著水桶就「嘩嘩嘩」撒了一泡尿,這才提起褲子對老蔫示意:「去!餵他們喝!」
老蔫為難地望向一旁的刀疤,卻見他並不制止,反而露出了饒有興致的微笑。老蔫無奈,只得舀上一瓢尿水遞到一個囚犯面前。只見那囚犯稍一猶豫,就閉上眼「咕嚕嚕」一口喝得乾乾淨淨。
眾差役哄堂大笑,還有人大聲調侃:「熱茶一定比涼水還要解渴吧?」
在眾人的哄笑聲中,老蔫一個個餵過去,只見眾囚犯有的麻木,有的哭喪著臉,有的則兩眼怒火。不過在極度飢渴之下,幾個囚犯還是毫不猶豫地喝了下去。
老蔫餵到最後一個囚犯時,卻見他別開了頭,一臉倔傲。老蔫嘆了口氣:「喝吧,從這裡過去數百里都是戈壁荒漠,不喝水怎麼成?」
「我是人,怎麼能不要尊嚴?」那囚犯澀聲道。他的聲音雖因乾渴而嘶啞難聞,卻依然透出一股不容輕辱的傲氣。
尊嚴?老蔫一怔,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更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囚犯。他不由細細打量對方,只見那囚犯身形瘦弱,看眼神似乎十分年輕,雖然鬚髮散亂,滿臉骯髒不堪,卻依然掩不住骨子裡的書卷氣。老蔫還想再勸,就聽身後的刀疤大聲問:「怎麼回事?他怎麼不喝?」
老蔫為難地回過頭,還沒來得及向刀疤解釋,刀疤已大步過來,一把搶過老蔫手中的水瓢,吐了口濃痰在裡面,往那囚犯嘴邊一遞,「嫌料不夠,老子再給你加點!」
那囚犯別開頭,一臉倔傲,雖然披枷帶鎖,他眼中依然有一種不容輕辱的傲氣,與其他囚犯那種卑微膽怯的眼神完全不同。這眼神刺激了刀疤,倏地一把抓住他的髮髻,迫使他揚臉向著自己,然後把手中的水瓢強塞到他口中,斥罵道:「不識抬舉的東西,還要老子親自伺候你?」
那囚犯使力一掙,把水瓢撞落到地。刀疤勃然大怒,一腳將他踢倒在地,指著他喝問:「你為什麼不喝?你跟他們有什麼不同?」
那囚犯在地上掙扎著坐起來,嘴裡兀自道:「我是人,不是牲口!」
「人?」刀疤一把將那囚犯拎起來,「你他媽也敢自稱是人?你們這些垃圾,有哪個敢自稱是人?」
刀疤說著扔下那囚犯,舉起馬鞭從幾個囚犯頭上一個個抽將過去,邊抽邊罵:「你!一個拐賣小孩的人販子;你!一個強姦女人的採花賊;還有你!一個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你們他媽的垃圾,有哪個配稱為人?老子恨不得將你們一個個就地處決,免得連累老子在這種天氣,還要伺候你們去青海旅遊!」
刀疤說著轉回到方才那囚犯面前,舉鞭抽道:「尤其是你!不僅強姦殺人,還坑蒙拐騙。老子真搞不懂,以你的罪名,就算判個凌遲也不過分,你他媽居然還能活命,真不知使了什麼齷齪的手段,花了多少昧心銀子。聽說你以前還是個秀才,就憑這,就該罪加一等!」
「我沒有!」那囚犯突然聲嘶力竭地大叫起來,「我沒有強姦殺人,也沒有坑蒙拐騙。我是被冤枉的!」
「呿!每個囚犯對老子都是這麼說的。」刀疤說著重新舀了瓢尿水遞到那囚犯嘴邊,「老子再問你一次,喝不喝?」
那囚犯針鋒相對地迎著刀疤凶狠的目光:「我是人,不是牲口!」
刀疤勃然大怒,將尿水潑到那囚犯臉上,扔下水瓢怒道,「好!老子看你能撐到什麼時候!只要你能撐到明天,老子就承認你是人!」說完向手下一揮,「來人!把他給老子綁到栓馬樁上,看他能倔強到什麼時候!」
幾個衙役把那囚犯從陰涼處拖出來,七手八腳地綁到驛站外的栓馬樁上。頭頂日光正烈,地面沙礫發燙,在上烤下煎之下,正常人根本堅持不了多久。那囚犯舔著乾裂的嘴脣,緊閉上雙眼,在如火烈日烘烤下,雖然神情早已疲憊不堪,但臉上卻依然有一種不屈的孤傲。
「誰也不許給他送水!老子要看看他到底能撐多久!」刀疤說著對老蔫一招手,「準備乾糧草料,咱們明天一早再走。」
天漸漸黑下來,戈壁灘的白天熱如火燒,到了夜晚卻又十分寒冷。老蔫餵完騾馬後,正好經過栓著那囚犯的栓馬樁,老蔫不由提燈照了照,卻見那囚犯全身癱軟地掛在那木樁上,不知死活。老蔫慌忙過去一探鼻息,隱約試到還有一點細若游絲的呼吸。
老蔫暗自嘆息,又想起了這囚犯日間那憂悒而倔強的眼神,雖經歷萬般磨難,依舊孤傲不屈,這是其他囚犯眼裡沒有的神光。不知怎地,老蔫始終忘不掉這種眼神。如今這囚犯在烈日下苦撐半日,渾身早已嚴重失水,若再不喝水,一定撐不過今夜。
老蔫側耳聽聽驛站內的動靜,只聽到一片酣聲。日間的長途跋涉,早已令眾人疲憊不堪,天剛入夜就已盡數睡去。老蔫悄然去舀來一瓢清水,然後托起那囚犯的下頷,小心翼翼地將清水灌入囚犯口中。片刻後,只見他睫毛微顫,終於緩緩醒了過來。
「謝天謝地,我還怕你醒不過來。」老蔫嘴裡嘟囔著,還想繼續餵水,誰知那囚犯卻本能地轉頭避開。老蔫忙道,「別緊張,這是清水。」
那囚犯將信將疑地淺嘗了一口,這才將一瓢水急切地喝完。清水下肚,他的精神稍稍恢復了一些,乾涸的眼裡泛起點點淚花,對老蔫哽咽道:「老伯,多謝相救!我駱文佳若有出頭之日,定會報答老伯一水之恩!」
老蔫擺擺手:「什麼報答不報答,等你活著離開青海再說吧。據我所知,凡發配到這兒來服苦役的囚犯,還沒有人能活著離開。」
那囚犯一怔:「這是為何?」
老蔫嘆道:「寧肯地上死,不要井下生。在礦井服苦役,吃的是陽間飯,幹的是陰間活。一年下來不知要活埋多少漢子?凡是被發配到那兒的囚犯,要麼在井下被埋,要麼被繁重的勞役折磨至死,幾乎無一例外。」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那囚犯眼中閃出駭人的光芒,「我是被冤枉的!我一定要活下去!我還要練成絕世武功,讓那些陷害我的傢伙付出應有的代價!」
老蔫同情地望著這個與眾不同的囚犯,卻不敢出手放他走。只見他拚命掙扎,似乎想掙脫身上的束縛,不過他的努力沒有撼動栓馬樁,反而令疲憊不堪的他一陣暈眩,渾身一軟便暈了過去。
駱、文、佳。老蔫在心中默念著他的名字,暗自嘆息:看來確實是個讀書人,只可惜,在惡劣的環境下,讀書人活下來的機會更是小之又小。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昏迷中,駱文佳的嘴裡還在喃喃念叨著,他那骯髒不堪的臉上,閃爍著異樣的神采,時而猙獰,時而溫柔,時而憤怒,他的意識似乎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過去……
尺寸(公分)21x14.8x3.5
開本 25
頁數 544
◆《千門(一):千門之門》
楔子
第一章 蛇禍
第二章 陷阱
第三章 蒙冤
第四章 暗獄
第五章 新生
第六章 逃獄
第七章 刀客
第八章 魔門
第九章 同行
第十章 佈局
第十一章 演戲
第十二章 奪經
◆《千門(二):千門之花》
第十三章 變故
第十四章 神捕
第十五章 伏罪
第十六章 自殘
第十七章 復仇
第十八章 莫爺
第十九章 對手
第二十章 反千
第二十一章 少林
第二十二章 奪寶
第二十三章 千雄


(二)-500x500.jpg)
千門之門+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千門之花+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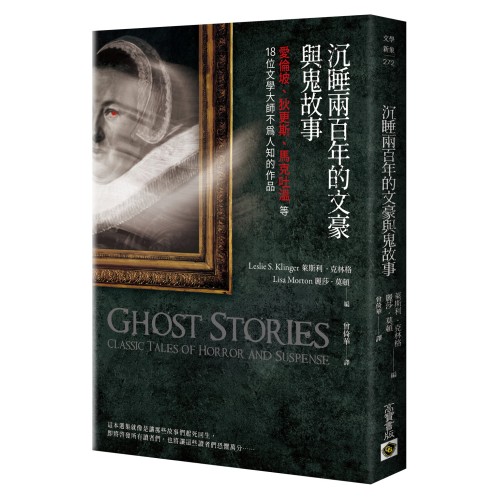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